
执行仲裁裁决中的公共政策考量是个极为复杂的权衡取舍过程。无论在大陆法国家还是英美法国家,“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似乎都是通用的裁量方法。赵芳律师通过分析英国上诉法院在RBRG v. Sinocore案中采取的立场,揭示了英国法官对公共政策的深刻认识。
英国法下的公共政策考量
——浅谈CIETAC裁决在英国被执行一案
赵 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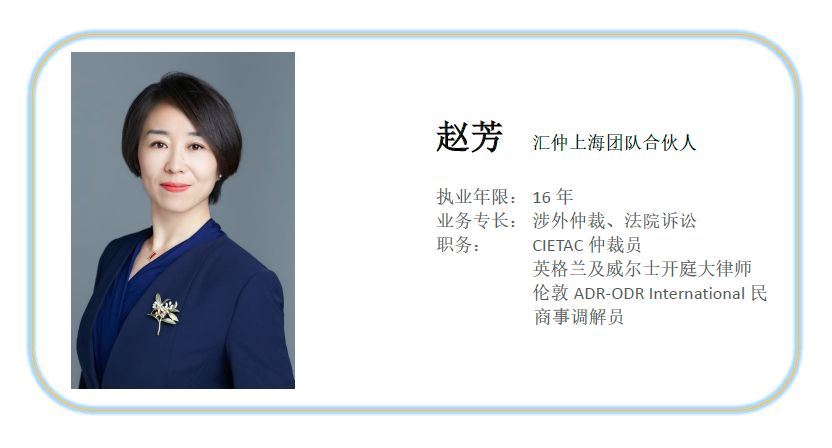
2018年4月23日,英国上诉法院对中国法律界非常关注的RBRG v. Sinocore不予执行CIETAC仲裁裁决一案作出二审判决,判决驳回了RBRG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申请,并维持了此前高院作出的执行CIETAC仲裁裁决的法庭命令。
本案判决一出,在国内法律界也引起颇多波澜。大家一方面对英国法院大力支持国际仲裁的作法表示十分赞叹,另一方面也不免疑惑,特别是对判决第40段所写的“公共政策考量”存在颇多不解之处。因为在这第40段中,Lord Justice Hamblen 写道:“本案并不涉及公共政策。即便涉及,(仲裁)终局性的重要性也超越其他任何公共政策考量。[1]”任何人初读此句,第一感觉都会觉得法官是不是写得太过了,把仲裁终局性也看得太重了。
但是,如果细读判决原文,则会发现这种看法大约是多虑了。三位Lord Justices一致同意一审判决,并在二审判决第40段中作出这种表述其实是有前因后果的。判决40段之前已经对于何为公共政策,以及如何对各种公共政策进行权衡考量进行了大量说理和铺垫。所以,放在上下文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下综合理解第40段的话,就不会再有“过激”的感觉。
为了彰显写得非常精彩的二审判决中的思想精华,在此我简要地写一写个人读后感。希望对大家理解英国法下的公共政策有所帮助,也希望这种公共政策考量能够在合适处为国内司法所借鉴。
案件相关事实
1. 2010年4月,Sinocore和RBRG签订了一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Sinocore为卖方,RBRG为买方。双方约定合同下货物应最晚于2010年7月从中国运往墨西哥,同时约定RBRG应开立不可撤销信用证支付100%货款。
2. 双方约定合同的实体准据法为中国法,并约定了仲裁条款,即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均应交由CIETAC在北京仲裁解决。
3. 2010年5月,双方修订过一次合同,同意RBRG在货物发运前进行货物检验。
4. 2010年4月,RBRG在荷兰Robobank开立信用证,信用证规定的货物最晚发运时间为2010年7月31日。信用证受UPC600管辖。
5. 2010年6月,Robobank根据RBRG单方指示,修改了信用证条款,将货物发运时间改为具体期间,即“7月20日至30日之间”。该条款修改未经过Sinocore同意,因此依照UPC600第10条为无效修改。
6. Sinocore在7月5日和6日实际装运了货物,并出具了相应提单。7月7日货物发运。同日,Sinocore书面告知RBRG货物已于当天发运。
7. 2010年7月22日,Robobank收到代收行转交的Sinocore信用证索付文件,其中包括日期为7月20日和21日的提单。由于货物是7月5日和6日装运的,很显然这些提单是伪造的。于是RBRG向荷兰法院提出禁令申请,要求不支付信用证下款项。而荷兰法院也接受了申请,颁布临时禁令禁止开证行Robobank支付信用证项下的款项。Sinocore因此未获得信用证下货款,并不得不后续将货物以亏本的价格转售。
8. 2010年8月13日,Sinocore在北京一中院向Robobank提起诉讼,索付信用证下货款。同年8月20日,Sinocore向RBRG发出合同解除通知,主张RBRG违反合同并保留索赔权利。RBRG收到通知后同意合同解除,但保留向Sinocore主张违约赔偿的权利。
9. 2012年4月,RBRG向CIETAC提出仲裁申请,主张Sinocore违反合同下货物检验约定,并请求赔偿。RBRG认为,Sinocore提前发运货物就是为了阻止RBRG检验(本就存在瑕疵的)货物,其后续伪造提单就是为了掩盖这一事实。
10. Sinocore在仲裁下提出反请求,请求赔偿货物原价和其后续转卖货物销售价之间的差价。
11. 2014年6月30日,CIETAC作出仲裁裁决,驳回RBRG请求,并支持了Sinocore的反请求。仲裁庭的裁决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条:
1) 合同履行过程中,RBRG没有提出过货物检验的要求,因此Sinocore没有违反合同。此外,双方在合同下的争议核心并不是货物质量,而是信用证修改是否符合双方所签署的货物买卖合同。
2) 由于Sinocore并没有同意修改信用证条款,因此RBRG单方修改无效,且修改与双方之间买卖合同不符。RBRG单方修改信用证的行为构成违约,同时该行为导致Sinocore未能获得货款,致使Sinocore解除双方之间买卖合同。
3) 仲裁庭表明其对提单是否系伪造并没有管辖权,因为提单伪造是Robobank和Sinocore之间的问题。但是,仲裁庭认为,即使Sinocore确实伪造了提单,其所欺诈的也是Robobank而并不是RBRG,因为RBRG从头到尾都知道货物何时发运。同时仲裁庭认为,本案下Sinocore的欺诈并非争议焦点,也不是导致Sinocore索赔的原因。导致Sinocore损失的根本原因,是RBRG单方修改信用证的违约行为。
12. 裁决作出后,RBRG曾经试图在北京市二中院撤销裁决,但其申请被驳回。2016年2月15日,Sinocore在英国伦敦申请执行CIETAC裁决,要求RBRG支付裁决下4,857,500美元的赔偿金,高等法院于2016年3月2日发出法院令同意执行,但该法院令同时声明RBRG可以在收到法院令之日起14日内申请撤销该法院令并附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
13. 2016年3月18日,RBRG根据《1996年仲裁法》s.103(3),向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High Court of Justice Queen’s Bench)申请撤销执行仲裁的法院令。2017年2月17日,高等法院的Justice Phillips驳回了RBRG的申请。一审判决理由主要有两点:
1) Sinocore和RBRG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本身和欺诈无任何关联,也无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同时,CIETAC裁决和Sinocore伪造提单向开证银行请款的事宜没有直接关联。裁决书认定的是RBRG违约,因而需要支付合同下赔偿款。
2) “欺诈推翻一切”该法谚在本案下只适用于Robobank和Sinocore之间,即银行在任何情况下不应依据伪造单据付款。但是,并没有任何判例显示,Sinocore不能就其提交伪造提单之前RBRG已经实施的在先违约寻求救济。RBRG主张Sinocore的欺诈行为“污染”(taint)了裁决书并要求不予执行裁决的作法会导致不确定性,并破坏缔约方的意思自治。
14. RBRG随后上诉至英国上诉法院,提出四条上诉理由,其中前三条理由比较重要:第一,一审法官在判定Sinocore“非法行为”(illegality)时适用了错误的判例,即适用Tinsley v Milligan下的狭义理论;第二,法院应该适用Patel v Mirza下的广义理论判定“非法行为”;第三,法官错误地认定Sinocore在仲裁程序中的请求未基于其非法行为。
15. 2018年4月23日,上诉法院Lord Justice Hamblen主笔判决,LJJ. Lewison和Irwin同意LJ Hamblen判决理由,最终驳回RBRG的全部主张。
本案涉及的公共政策
RBRG提出撤销法院令的依据是《1996年仲裁法》s.103(3),即如与公共政策相悖,法院可考虑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2]。在本案下,RBRG主张承认和执行CIETAC裁决与英国公共政策相悖,因为执行该裁决将事实上协助Sinocore的商业欺诈行为。英国衡平法下有一条法谚即“欺诈推翻一切”(Fraud unravels all),同时普通法下也有一条法律原则即“禁止非法主张”(Ex turpi causa)。RBRG认为根据这两条原则,法院不能协助进行了商业欺诈的Sinocore基于其非法行为主张合同下赔偿。如果法院这样做,将有违公共政策。
欺诈
在英国法下,欺诈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对开庭大律师而言,必须遵守的基本职业道德之一就是没有客户明确指示不能主张对方当事人进行了欺诈。即使有客户指示,除非有合理的证据证明欺诈存在,律师也不可以协助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欺诈的主张,而应向当事人进行说明。如果当事人不听从律师建议,非要在没有证据或显著缺乏合理证据的情况下提出欺诈主张,则律师需要考虑解除委托,否则律师会违反对法庭的义务。这一系列的要求表明,在英国法下,欺诈是一项需要极度审慎才能提出的主张;另一方面,这些要求也显示了欺诈主张成立的难度要求很高。
但相应的,欺诈一旦成立,后果当然也是非常严重的。在欺诈成立情况下,被欺诈的一方可以依法得到比较充分的救济,而在欺诈导致的损害证明方面,举证要求也比一般的合同之诉下的要求低。这是因为考虑到欺诈的特殊性,为了防止和禁止欺诈,英国法认为有必要给欺诈方一定程度的惩罚,因此需要采取非同一般的政策倾斜。这也是“欺诈推翻一切”(Fraud unravels all)基本原则的由来。
非法行为
“禁止非法主张”即Ex turpi causa,指原告如果要主张一项权利,而该权利是依据其非法行为所产生的,则法律禁止其主张这个权利。因为法律不支持非法行为。
RBRG这个案件所涉及的一个重要的上议院判例Tinsley v Milligan [3] 即与Ex turpi causa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在Tinsley一案中,原告Tinsley和被告Milligan是一对同性恋人,她们共同出资购买了一栋房产,但产权登记在Tinsley一人名下。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Milligan名下如有财产就不能向社保机构申领福利补贴。因此,双方这种产权登记安排是为了实现非法目的——骗取社保福利。后来Tinsley和Milligan分手,Tinsley提出诉讼,主张房产产权完整归属于她;而Milligan提出反诉,要求确认其在房产下的部分权益。这个案子一路打到当时的最高司法机构上议院,最后上议院五个大法官以三票赞成两票反对,支持了Milligan的主张,驳回了Tinsley的请求。
赞成派的理由很巧妙:因为Milligan在购买房产时出资了,所以她当然享有房产下的权益。她的权益无需以非法骗取社保福利的安排为基础,因为只要出资就能享有房产权利,这是法定权利[4]。与此相反,Tinsley只出资了部分,她要获得全部产权的依据是当时双方同意为了骗取社保而把产权登记在她一人名下。所以Tinsley要享有完整房产权利,需要法官确认当时双方的这种登记安排合法有效。根据Ex turpi causa原则,因为双方的安排是为了骗取社保,是非法行为,所以法院不应支持Tinsley的主张。既然不支持Tinsley的主张,那么Milligan的主张就得到了支持。
反对派的理由其实也非常有道理。反对的大法官认为,Tinsley和Milligan之间的非法安排法院不应干涉。因为不论如何Milligan都是涉足非法安排的一方,支持Milligan的请求等同于支持她曾经的非法安排,这不利于正确引导公众价值观。相反,如果法官不干涉,保持原状,则Tinsley无非类似天上掉馅饼而捡了个便宜(obtaining windfall),但这也是Milligan咎由自取。在允许Tinsley不当得利和正确引导公众两种取向之间,法院应取其大者,所以法院应该保持现状不予干涉,以警示未来想要如此进行非法安排的人,预示风险。
Tinsley一案作为最高司法机构的判例,饱受各界批评。批评理由大致和反对派的两位大法官在判决反对意见中提示的问题一致。因此,在2016年,英国最高法院通过Patel v. Mirza[5]一案推翻了Tinsley,宣告Tinsley原则不再普遍适用。Patel的案情无关紧要,但其确立的原则是,法官面对类似Tinsley一案的涉嫌非法行为的请求,需要考虑三点:
1)原告原本意图绕行何种法律禁令,驳回原告的请求是否会使得这种法律禁令被更好地遵守;
2)驳回原告请求是否会对其他相关的公共政策产生影响;
3)驳回原告请求是否是对其非法行为的一种恰当的回应。
也就是说,Patel一案其实是将Tinsley下的原本比较技术化的公式,即只要原告请求不直接依据非法行为即可被支持,改为以上三项灵活大原则,由法官根据千变万化的事实情况具体去分析和把握。在RBRG一案中,RBRG也援引了Patel作为其法律依据。
由Tinsley和Patel两案其实可以看出,英国的大法官在进行判决之前,总是对案件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双向分析,最后衡量哪种公共利益更需要得到保护。事实上,每个案子下的利益都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重合的。比如Tinsley/Milligan的房产权利涉及个人财产权的保护,这同时是一种公共利益;而否定某些个人利益,是因为公共政策不鼓励非法行为,这是另一个层面公共利益的需要。在两重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必须要分析哪种利益对于公众更根本、更值得保护。
以上视角实际上与RBRG案下的公共政策分析密切相关。
执行仲裁裁决
执行仲裁裁决事实上也是英国法下的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而这项重要的公共政策首先反映在《1996年仲裁法》s.103条中:除非出现s.103(3)规定的特殊情况,法院必须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s.103下的这一原则已为多个判例和学术典籍所遵循采纳,并有很多经典论述,例如IPOC (Nigeria) v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6], Mustill & Boyd[7]等。
本案下上诉法院的公共政策考量
RBRG一案一审时,一审法院开宗明义,在判决中首先说明了“执行仲裁裁决”是英国法下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同时继续分析了“欺诈”和“非法行为”这两项公共政策考量对于执行仲裁裁决公共政策的影响。
二审判决中,上诉法院延续了一审法院的基本思路。
上诉法院首先阐明了《1996年仲裁法》s.103(3)的含义,即在该款下,执行仲裁裁决的大原则只在违背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才不适用。
上诉法院同时援引了Dicey, Morris & Collins第15版的《冲突法》(The Conflict of Laws),对何种情况下英国法院会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进行了总结。与RBRG一案相关的有以下四种情况:
1) 《1996年仲裁法》s.103(3)下的“公共政策”应当作非常限制性的解释。因为执行仲裁裁决本身也是一项公共政策,这项公共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纽约公约的目的。因此,即使存在一些与执行裁决政策相悖的其他公共政策考量,法官也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执行裁决。
2) 当仲裁庭对是否存在“非法行为”的问题具有管辖权,除非极端情况,英国法院不应当对事实问题进行重新审理。因为正如Mustill & Boyd在2001 Companion 95页所说:国际仲裁的原则之一,就是即使执行地的法官对裁决所涉问题有一些法律上的不同考虑,他也要相信外国仲裁员和法院地法官的原始判断。也就是说,除非出现极个别情况,法院不应对仲裁裁决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实体考察。
3) 当考虑是否执行仲裁裁决时,如果裁决适用的准据法(governing law)不认为裁决下存在“非法行为”,而英国法认为存在“非法行为”,则法院有自由裁量权拒绝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但是,在此情况下,法院对于裁决下非法行为的考量必须限于“国际公共秩序”,而非英国国内公共秩序。即如同一审法院Phillips J 援引Lemenda[8]一案中的语句,该等公共政策必须“放之四海而皆准”(based on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
4)在决定执行裁决是否会涉及公共政策时,被请求执行的裁决内容和“非法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和程度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Soleimany[9]一案下,仲裁庭所裁决的合同涉及将货物走私出伊朗,因此该合同非法,而这种非法性也是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据此英国法院拒绝执行裁决。而作为对比,在Wilson v Hurstanger[10]一案中,虽然裁决下的合同是一方涉嫌贿赂而获得签署的,但是合同本身是合法的合同,所以英国法院执行了仲裁裁决。法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法院在执行合法合同方面一直都采取比较大的力度。因为英国法力求保护当事人在合法合同下利益,力求维持合同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在英国法下,合同本身不合法,和当事人采取了不当手段签署了合法合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如果无辜的一方希望履行合法合同,法院应当维持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如何惩罚采取非法手段签署合同的一方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无辜的一方不想维持合同,且非法手段确实会导致合同可撤销,则法院才会采取其他方式另行处理。
总而言之一句话,维持合法合同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也是英国法下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
基于上述原则,上诉法院在二审中一一否决了RBRG提出的与欺诈、非法性和公共政策相关的主张,法官的主要思路可概括如下:
1)Patel这个案例和s.103虽然不矛盾,但同时也可以说无关。因为在Patel一案之前,英国法下对于实体请求(substantiveclaim)和仲裁裁决执行采取的是不同的判定标准。最高院在Patel判决中也没有提到这个判决会和s.103相关,因此本案不应当适用Patel。
2)RBRG在上诉中的主张,其实质始终是要求法院重审仲裁庭在裁决中已认定的事实问题,上诉法院和一审法院均认为,这在本案中是不恰当的。同时,即使法院同意重审事实,RBRG的法律立场也很弱。因为仲裁庭认定了RBRG修改信用证并没有经过Sinocore的同意。既然如此,RBRG的立场只能是:Sinocore要获得买卖合同下的款项,应当提供符合原信用证要求的单据。就算Sinocore能提供这些单据,也没法获得原信用证下付款,因为信用证已经被RBRG修改了。法官因此认为RBRG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
3)在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考量的是执行“裁决”,而非执行“裁决下的合同”。如果仲裁庭有合理理由认为裁决下的合同并不违反合同所适用的准据法,即使法院根据英国法对于同等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也不能得出结论认为裁决违反了英国的公共政策。但在本案下,无论如何法官看不出裁决下合同有任何违反中国法或者英国法的情形。
4)已有多个重要的案例显示,执行仲裁裁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公共政策,而本案不存在可以推翻这项公共政策的理由,具体而言:
a. CIETAC裁决下不存在欺诈,只有欺诈未遂。因为Sinocore虽然提交了伪造的提单,但是RBRG和Robobank都没有受骗上当。自始至终,信用证下的款项未能给付。
b. 仲裁庭明确表明了合同下的核心争议不是欺诈本身(仲裁庭也未对是否构成欺诈进行查核),而是RBRG未经同意而单方修改的信用证是否符合双方的买卖合同。
c. 正如一审法官所明确的,虽然Sinocore提交了伪造的提单,这是一个非法行为,但是并没有任何在先判例表明,Sinocore不能针对其提交伪造提单之前RBRG单方修改信用证的在先违约行为获得救济。
正是在上述逻辑非常严密、完整的讨论之下,Lord Justice Hamblen才得出了判决第40段中的结论:本案不涉及公共政策,即使涉及,(仲裁)终局性的重要性也超越其他任何公共政策考量。
我个人对Lord Justice Hamblen这句话的理解是:CIETAC的这份裁决,既不涉及欺诈,也不涉及Ex turpi causa类型的非法行为[11],所以不应被拒绝执行。相反,即使CIETAC裁决中当事人涉嫌欺诈或者非法行为,因为裁决书下存在一份合法合同,Sinocore的欺诈或者非法行为并未推翻合同本身的合法性,Sinocore的仲裁请求是基于合法合同的约定提出来的,其主张执行的请求与被指称的不法行为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联度。同时,Sinocore在裁决下请求的实质是要求履行这份合法合同,承认CIETAC这份裁决的终局性并加以执行,体现了英国法下维持合法合同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一贯政策。在此情况下,如果法院拒绝执行这份裁决,一会影响裁决下合法合同的可履行性,侵害英国法下的一项重要公共政策,二会违反依照纽约公约执行仲裁裁决的大原则,侵害英国法下的另一项重要公共政策。据此,就算Sinocore曾经意图欺诈,两害相权取其轻,执行仲裁裁决所能够保护的公共政策将更为重要。
结语
由上案件可知,“Fraud unravels all”虽然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衡平法原则,但在实践之中却不是一柄万试万灵的尚方宝剑。英国法院对于“欺诈”指控始终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不会轻易判定欺诈成立,更不会随便unravels all。这是因为“维持合同合法有效可履行以及法律的确定性”也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商业原则,代表了同等重要的公共政策。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法院不会随便应用“欺诈”来推翻合同。
同时,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在哪个法律系统下,法律的本质都是朴实无华的。Sinocore v RBRG这个案子,单看事实部分,大部分人本着朴素的价值观都能得出和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同等的结论。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两份判决,虽然均高屋建瓴、旁征博引,援引了大量的案例和法律原则,进行了复杂的说理,但最后的落脚点依旧是“公平合理”两词。而这公平合理二字是RBRG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包装自己的观点,都始终无法绕行的。
总而言之,阅读这两份判决书,再次让我清晰地感觉到,英国法院对于私人利益的保护总是建立在对立公共政策的取舍之下,同时彰显了英国法追求法律稳定性和确定性的基本原则。而这种对于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关注,同样值得我们大力学习。
[1] 原文为:“Inthose circumstances, public policy is not engaged. Alternatively, if it isengaged, any public policy considerations are clearly outweighed by theinterests of finality, as the judge held.”
[2] S.103(3)原文:103 Refusal of 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of a New York Convention award shall not be refused except in the followingcases…recognition or enforcement of the award may also be refused…if it wouldbe contrary to public policy to recognise or enforce the award.
[3] [1994] 1 A.C. 340
[4] 在英国信托法下有一种叫做resulting trust的法定信托安排。在这种信托下,如果一方和另一方无亲属亲缘关系,一方出资购买的房产,由另一方登记享有权利,法律将直接认为登记方作为受信托人为出资方的利益持有房产权。因为法律认为,没人会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赠与。因此如果无对价,未出资的一方不能直接获得房产权,双方之间的安排构成法定信托。未出资方持有的利益应返回(resulting)给出资方。
[5] [2016] UKSC 42
[6] [2005] 2 Lloyd’s Rep 326
[7] Page 91-92
[8] [1998] 1 Lloyd’s Rep 361
[9] [1999] Q.B.785
[10] [2007] 1 WLR 2351
[11] 因为Sinocore在仲裁中主张货款差价不以欺诈行为为依据,所以不存在Ex turpi causa.
(撰稿:赵芳 汇仲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配图:肖臣宸 汇仲律师事务所律师)
 声明: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可视为汇仲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或需要法律意见,请与本所联系。
声明: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可视为汇仲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或需要法律意见,请与本所联系。
汇仲律师事务所的网址为:www.huizhonglaw.com
汇仲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为:huizhonglawfirm。
欢迎关注及浏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