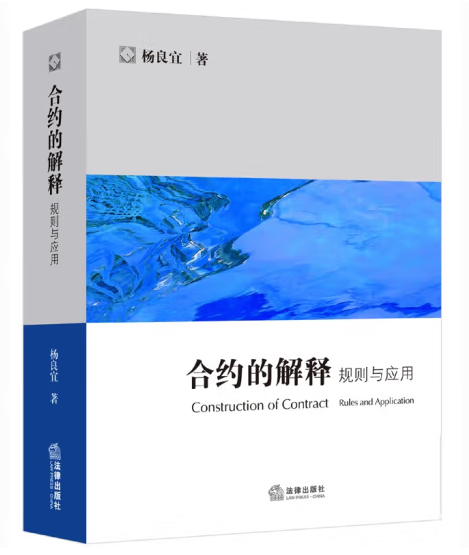
一、本提问与仲裁法关联不大,但可能涉及合同法和证据法。
a公司向b公司订购模具,但双方没有签订合同,b公司负责人手机意外丢失,导致相关微信聊天记录也丢失,b公司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因为ab公司之间的其他争议,b公司以模具数量为5台、价格为15万元/台向a公司提起反诉,庭审中a公司律师称“我方向b公司购买模具,属实,但b公司至今未将合格的模具交付给我方,所以我方无需承担付款责任。”请问根据英格兰证据法,a公司这段答辩是否就数量和价格构成自认(admission)?根据英格兰合同法(假设适用),如何解释这段答辩的真实意思?
答:这一个问题的确是不适合在国际仲裁的系列课程中提出,应是在合同法或证据法课程中提出。但这也无妨,能够全盘掌握系列课程就任何实务问题都可以串起来,毕竟这三门课程构成一套基础 。
首先讲讲这问题的次要几个方面 :
(i) “没有签订合同”与是否达成有效合同没有关系,合同完全可以通过言行达成,在日常生活中或国际商业中的小额交易很少是会涉及双方的“签订”,这在一份简式合同只是例行手续。
(ii) b失去了手机,但a不会也同时失去吧?所以微信记录完全可以在相互披露的诉讼/仲裁程序中要求a披露。而如果a也这么巧同时失去了手机(与其他所有同步过相关记录的存档),仍可以向法院申请“第三方披露令”要求存有记录的第三方提供有关证据(但据悉由于采用端到端技术及中国数据保护立法等原因 ,腾讯宣称微信用户的聊天记录不会在其服务器/数据库中保存,因此针对微信聊天记录要求腾讯披露看来存在困难 )。
接下去是这问题的主要方面:
(1) 如果a代表律师称“属实”,这明确是“自认/承认”(admission),一旦双方承认的事实,就对该“事实”再也没有争议,法院/仲裁庭必须接受这是“事实真相”,也无需任何证据了。
(2) 但这问题指a代表律师是在庭审时才 “自认 ”,就可以推测出这会是内地诉讼或仲裁才会出现这么迟的自认/承认,因为内地的诉讼/仲裁几乎没有什么中间程序或有关人士不太理解每步程序背后的意义与正确做法 。如果在国际仲裁或法院诉讼(在香港特区或伦敦),早在文书请求(pleadings)的第一步就要求双方明确了什么是争议或相互承认的事实。所以b在反诉是主张与a有合同与合同是什么内容,a就要在对反诉抗辩 (statement of defence to counterclaim)中明确是否对此主张“自认/承认”。如果a只是粗略说“ 否认”(bare denial)此主张,这也不被允许或视为是承认,回避与没有针对的也会被视为是承认(经常遇到中国律师这样做,不逐个针对对方的主张)。a是必须说明否认的事实依据 ,如根本不认识b或双方在微信的谈判谈崩了,根本不存在合同。一旦在文书请求阶段双方已经“自认/承认”,在接下去的证据程序(evidential steps),如相互文件披露、证人证言、 庭审等等,就无须再去针对该“事实真相”了,根本不会发生直到庭审时a代表律师才“ 自认”的情况 。更不说还要看是什么性质的“自认/承认”, 一些对重要与核心事实的“自认/承认” 会让对方b马上申请提前撤销索赔或抗辩,法院或仲裁庭对“自认” 部分可以作出简易判决或裁决书( 今天像HKIAC或SIAC等仲裁规则都增加了仲裁员在这方面的权力)。
如果一方不肯面对现实而拒绝在文书请求中拒绝承认赖不掉的事实,在文书请求之后对方可要求该方承认事实(notice to admit fact)(可以参考 《证据法——国际规管与诉讼中的证据攻防》一书第七章之10.2段。
二、如果仲裁协议中对仲裁语言约定“Chinese and/or English”,在仲裁程序中(包括提交证据)是否以下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都会被接受:中文,英文,中英文。
答:这样的约定并不够肯定与明确,就文字本身去解释条文也的确是三种情况都可以,但现实中大家总是要同意或仲裁庭决定一种操作。如果是中英文双语,那在操作中就会面对不少麻烦与困难,例如,是否大量披露的文件(可以是中、英或其他语言)或作出的裁决书都要同时以两种语言呈现?开庭时每个人说每句话都要以两种语言说两遍?这会耗费大量时间与金钱。但更重要不可行是一旦开始了仲裁并成立了仲裁庭,总会在双方的律师团队或仲裁庭的三位成员之间有个别人懂双语,但也有人(尤其是仲裁庭成员)只懂一种语言(是一位老外)。
这一来,其中一方当事人只提交中文的文件证据或文书请求,是其中一位仲裁员看不懂的,就肯定不可行了,因为他无法去审理 。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双方会针对该仲裁案件的特定情况(如仲裁庭成员有不懂中文的老外)讨论与同意可行的做法,如以英文作为仲裁语言,可以省费用与省麻烦。又或是,双方都是中国公司与仲裁庭都是懂双语或中国人,就以中文作为仲裁语言。
但也有情况是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这情况会是如:(1) 一方缺席;(2) 其中一方意气用事,不懂、希望以不合作或扯皮令对方知难而退(其实不会发生 )。这一来,就会是要仲裁庭来作出决定了。本来如果双方明确约定了仲裁语言,仲裁庭必须依从,没有裁量权去作出改变。但在此仲裁协议,由于不够肯定,仲裁庭在有法律责任去省钱与省时间推进仲裁下,会是看情況决定以中文、或英文、或双语作为仲裁语言进行,这都有可能,也不违反双方的约定。在国际仲裁中,仲裁庭决定以英文进行仲裁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一般是大家都多少懂英语(因为国际通用)。
三、临时仲裁和“三特定仲裁”有哪些区别?除了程序的完全灵活性,临时仲裁有什么核心要素呢?
答:你指的“三特定仲裁”(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在内地特定地点、按照特定仲裁规则、由特定人员对有关争议进行仲裁)是国际仲裁不会关心的“创新”说法。据悉,这“创新”是中国试图在自贸区开放临时仲裁,但又怕放得太开,所以有三个特定,而且目前也没有一宗三特定的仲裁案件,我也不相信会有,因为一加了“特定”就带来不肯定与不稳定,现实的商人或代表律师是不会找麻烦去作出新尝试。例如,什么是“特定仲裁规则”?是UNCITRAL Model Rules?如果是,国际海事仲裁大部分都是临时仲裁案件,会否也包括一些海事仲裁规则如HKMAG Rules, SCMA Rules或LMAA Terms?又或是,什么是“特定人员”?
国际上,“临时仲裁”(ad hoc arbitration)的核心只是与“机构仲裁”相区别,就是是否存在机构管理。至于中国自贸区搞出来的“三特定仲裁”或将来去多加几个特定变为“四特定”或“五特定”仲裁,这区别是要对这些“特定”给出具体内容与规则,加上大量案例的解释后才能知道了,这可能遥遥无期。
至于临时仲裁(甚至是任何形式的仲裁),目前在中国推行恐怕也不会成功,因为其他不配套与达标。例如,中国仲裁法中院对仲裁的监督仅仅局限在 : (1) 仲裁协议的效力;(2) 仲裁裁决的执行。而仲裁庭在中间程序/证据程序的决定(甚至很多决定是由办案秘书去处理,顶多会与首席仲裁委员商讨后才决定,而两位边裁往不会知道情况,逞论去作出决定),在中国的仲裁法下是欠缺法院的监督的,而是让各个不同的仲裁机构去决定与监督。但国际上的仲裁(也包括临时仲裁),中间程序都是由仲裁庭自己来决定与受仲裁地法院的监督,以防止仲裁员灵活处理中间程序时作出的决定是乱来与严重违反程序公正(due process)/公平审理( fair trial)。这监督包括当事人去法院申请把该不妥的仲裁员在临时仲裁程序进行中赶走,而不用等到已失去信任的仲裁员在开庭审理与作出裁决后才去申请法院把裁决书撤销,因为这延误的救济会带来大量的金钱损失与时间的浪费。但中间程序无论是由仲裁机构办案秘书处理、或改革后(如北仲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的由仲裁庭直接处理、或仲裁法修改后允许没有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员来处理,那么谁来监督仲裁中间程序的自然公正与公平审理?谁能保证仲裁机构、秘书或仲裁庭不会“无法无天” (包括贪污受贿)或不懂去乱来?
四、 如果上海要建设类似伦敦、新加坡、香港的国际认可的仲裁地,您认为哪些方面最需要提升?
答:这可去节录近期发表的《国际仲裁中心是形成的》(司玉琢、王伟教授)一文的结语:“伦敦等国际仲裁中心的发展历程启示我们,任何解决争议中心都不是建成的,而是形成的。硬件可以建成,增加资金投入即可,软件则不行。仲裁服务的价值本质是高效公正的解决纠纷,这一价值的实现靠人才、法律、环境等一系列的软件叠加,软件需要靠长期的文化底蕴滋养,司法实务沉淀,靠优良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的保障;服务、效率、观念、意识等软实力是无法靠金钱实现的。”
我是完全认同这一个观点,也就是上海(或中国其他地方)如果想真正成为国际认可的仲裁地或中心(其他软件方面的中心如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商业中心等),先决条件就是有国际认可与有信心的,可以与国际跨国律师所的英美律师平起平坐对抗的人才。当然,今天对 “人才” 的称呼是被严重滥用了。但相信今天中央领导在大力呼吁培养涉外法律人才, 如习总书记在2019年2月2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涉外人才数量非常不足,这就可以见到在内地培养涉外法律的人才在这45年来(我是在1979年首次回来北京讲涉外法律/海商法,之后没有间断的一路关心与参与内地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虽然有大量的投入(例如中国有法学院的大学可以说是数量不少),但并不太成功。
这也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涉外法学教育欠缺培养思维的基础学科的学习,令这些进入国际商业或法律社会的中国法学生在面对千变万化的现实问题时缺乏基本的分析能力与没有指南针。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的高速发展,实践中有大量的机会去磨练,但因为欠缺基础,无法让中国在涉外法律方面好像自然科学一样能弯路超车。这也是我在这15年来系统性写出9本涵盖国际通用的合同法、证据法与国际仲裁的主要针对国际私法的书籍,与这5年来向各大学推广的系列课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学习涉外法律要走直路先把基础打好。
但在内地的大环境下,我多年来也只能是往前走一步,后退两步,摸着石头过河。只能说近十年来看到内地对涉外法律与国际仲裁懂行的健康势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比较乐观,相信假以时日是可以达到目的。
最后去一提的是要成为国际认可的仲裁中心,这“国际认可的人才”也不光是仲裁员、代表律师、仲裁机构等,也包括监督的法院、负责的官员、大学法学院老师、专家证人与当事人(也就是中国公司/企业的领导与法务等人)等等方面都有大量与越多越好的人才。他们一并努力与需要一定的时间(快也要5年10年,但期间是天天向上)才能去把相关的法律制度与营商环境等一系列的软件叠加起来,成为一个真正与屹立不倒的国际仲裁中心(与其他走在一起的软件方面的中心)。
五、仲裁当事人可以多大程度上排除法院的干预?双方协议即可?当事人该怎么考虑选择通过法院还是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另外仲裁决执行中,申请执行方是否可以通过同一家银行的境外分支机构来执行境内银行的资产?
答:可把上述问题扯开三个不同部份来解答:
(一)在这个问题,可以经验最丰富的伦敦仲裁为例来看在多大程度上可排除英国法院(作为监督法院)的干预。英国1996年《仲裁法》中规定了强制性(mandatory)与非强制性(non-mandatory )条文。而强制性条文的规定不能由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排除,也就是在英国公共政策上法院一定要监管(或干预),否则伦敦仲裁有危险在没有监管下,会很快沦落为无法天的洪荒之地。最著名的是该立法的第24条(赶走仲裁员)、第33条(仲裁员公平审理的责任)、第67条(对管辖权的质疑)、第68条(以严重违规为由撤销裁决)等。但第69条(对裁决中的法律问题上诉)是非强制性的,因为此立法条文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英国普通法/商法,没有必要强制外国当事人出钱出力来协助英国法律的发展,也不会是公共政策。因此,仲裁协议可以通过所谓的“排除条文” (exclusion clause )将69条的适用排除,比如说:裁决是“最终的和有约束力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再向法院上诉” (final and binding,neither party can further appeal to the Court)。
(二)至于申请临时措施(interim measures)的问题,确实在意图尽量减少法院对仲裁干涉的UNCITRAL Model Law后,在做法上才有所改变 ,首次将做出临时措施的权力下放给仲裁庭。在过去,当事人只能向法院申请临时措施。但是现在,在大多数仲裁地(伦敦、香港、新加坡等),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庭或法院申请临时措施,因为大家都有这方面权力。这方面是一个大课题,提出此问题的学员应去参阅有关书籍的章节,也就是《仲裁法—从1996年仲裁法到国际商务仲裁》一书之第十、十一章。其中 “考虑选择法院或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可见第十章之 2.2.1.2 段有关英国与3段有关香港特区针对法院与仲裁庭之间对临时措施的分工,内容太长无法重复。
显然,不少临时措施都十分紧急与发生在仲裁早期,例如需要马上保全证据,保全资产与各式样的禁令等,但不少仲裁机构光是在委任仲裁员与组成仲裁庭,往往至少需时2至3个月不等,而仲裁庭未组成就无法处理任何临时措施的申请。所以,这方面的申请大量仍是去法院,这才能对不少临时措施的申请人救急/救命。为了解决这个短板,不少国际仲裁机构也就推出了“ 紧急仲裁员” (emergency arbitrator)的做法。但不是所有仲裁机构都接受,例如LMAA在考虑是否纳入“紧急仲裁员”做法,结论是否定,因为:(1) LMAA针对的伦敦海事仲裁是临时仲裁,一般委任仲裁员与组成庭在时间上比机构仲裁要快得多了,有了仲裁庭就可以马上处理临时措施的申请。(2) 去英国法院更快、判决更准确,也更适合某些临时措施如单方面申请的冻结令或来不及提前通知对方的十分紧急的禁令。而紧急仲裁员相比效率高的英国法院仍会是太慢或太贵。(3) 伦敦作为国际银行、金融、商业等中心,英国法院去执行自己作出的临时措施命令应该十分容易。
所以问题中的当事人考虑选择向法院或仲裁庭申请临时措施会取决于:(1) 具体是什么临时措施?(2) 仲裁地点是哪里?例如约定了ICC仲裁与仲裁地是曼谷,在关心曼谷法院能否很快与很正确的去处理商业上的一些重要与紧急的临时措施申请,就可能会倾向选择ICC的紧急仲裁员做法了。(3) 向仲裁地的法院申请任何命令都会需要委任当地的律师,有些情况是外国当事人因为额外费用或设有适合人选而不想委任当地律师。
(三)第三个有关仲裁决书的执行的问题,这就与以上两个问题无关了,因为仲裁裁决书已经作出,仲裁庭就不再存在,也不再有什么临时措施了。确是,在一些金融中心,如伦敦或香港特区等申请一个全球冻结令,是惯常与非常有效的执行手段。在这种手段下,就是你的问题所提及的“通过同一家银行的一个境外分支机构 (如伦敦中国银行分行)来执行境内银行(北京中行)的资产 ”情况。
六、超裁后,可以要求仲裁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吗?
答:我不明白超裁为什么去扯上仲裁机构?这个问题反映了目前中国仲裁仍没有将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角色区分搞清楚的问题。国际上无论是机构仲裁还是临时仲裁,裁决书的决定是由仲裁庭做出,超裁应该是仲裁庭的事宜与责任,与仲裁机构无关。但超裁本质上只涉及专业疏忽,不会去扯上仲裁员贪污受贿等严重或刻意不当行为。这一来,香港特区或英国的仲裁法都免除了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无心之失或疏忽行为,这可见在香港 《仲裁条例》之104-105条或英国1996年《仲裁法》之Section74,不存在要求仲裁庭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
仲裁机构对仲裁庭超裁的疏忽行为也不需要负责,但会在其他管理仲裁案件时的言行中存在疏忽 (例如漏了给一方当事人通知)并带来责任,所以也是要立法去免除这种无心之失的责任。而法律会去立法免除他们的责任 ,也是为了支持国际仲裁,毕竟仲裁机构不是营利机构,没有什么钱可以赔偿。个别仲裁员在经济上也好不了太多,理论上他可以投保责任疏忽的风险,由于保险市场狭窄,市场也不会接受投保太高的金额,而今天的仲裁案件标的动不就是上亿或数十亿、百亿美元。仲裁员也是一个危险的行业,只要看今天中国败诉的企业与其代表律师,总是会敌意很深去责怪国际仲裁庭错判或偏袒,而不会自责自己不懂乱来或处理不好。所以有必要让仲裁员好像法院的仲裁法官一样,可以免除疏忽的责任。
但超裁一般是有足够的法律救济,受影响的当事人大可以及时向监督法院申请把超裁部分的裁决书撤销,无需动脑筋(也通常不会成功)去向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索赔损失。
七、 如果想要了解单边选择仲裁条文,是否有推荐的书籍或文章呢,单边选择仲裁条文在当下是否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争议问题呢,因为香港地区近年来似乎没有有关的案例。
答: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例子反映出学习国际仲裁从来不能只是局限在学仲裁程序本身,而更重要是了解国际合同法,因为除了仲裁中出的问题都是跟合同密不可分之外,更重要的是合同法会提供给大家找出核心问题或问题的本质的能力与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
单边选择仲裁条文或称“不对称仲裁协议”( asymmetric arbitration agreement)是指在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时双的权利不平等,例如只有一方可以选择仲裁或诉讼,而另一方则不能选择仲裁而只能去法院诉讼。这和不对称管辖条文都一样,就是一种合同的约定,和任何其他的合同约定一样。要去分析与解释该约定是否有效,都是在合同法的基础上出发,然后结合仲裁的特点,找出要注意的问题。如果合同法基础打了好,加上对仲裁程序的了解,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以下就以分析这个问题来展示一下合同法与仲裁法的结合与运用。
单边选择仲裁条文往往会出的问题就是在订约双方真的出现争议后,一方会以这个条文违反公平对等原则或约定不明确而提出无效或不可执行的争议。首先从合同法的角度来分析,法院对单边选择仲裁条文的解释与效力的认定。而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包括合同订立的要件(要约、接受、对价、有订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图和合意)没有满足,要么就是存在一些会令合同(或部分条文)无效或不能被强制履行的因素(包括欺诈、错误、胁迫、显失公平、非法等违反公共政策的事项、订立得自相矛盾无法协调、太模糊而无法执行、订约主体没有行为能力等等)。合同条文本身约定是否对双方公平从来不是一个可以令条文无效的理由。订约自由大原则是国际上普遍接受和认可的合同法精神。既然是订约自由,那么订立什么条文的可能性都有,其内容也是全面反映双方有舍有得的交易。即使个别条文存在对一方有利而对另外一方不利的不公平的情况,只要双方是你情我愿订立合同,不存在前述提到的令合同无效或不可执行的因素,法院都要尊重。这特别是在国际商业社会的层面,被广为接受的英国法是默示所有参于国际商业活动的人士(包括了发展中国家的国企/公司)在知识水平与谈判力量上都是平起平坐。所以,社会上会发生与承认的违反公平对等原则的一些救济如“显失公平交易”或“不当影响”是不适用在国际商事争议,只会发生在如与未成年人、文盲、痴呆老人订立的合同。
而订约方订立这样的单边选择仲裁条文,也往往是有特别的考虑,例如这种条文经常出现在金融合同中,借款或提供融资的银行希望他们向债务人追偿时可以不受限制的去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管辖与争议解决方式,而债务人则不被允许有这样的选择权,所以特别订立不对称的管辖条文或仲裁条文,而这是经过双方商谈后而一致同意的。在跨国银行按照一些全面保障自己的格式条文去强势订立的金融合同,又何止是不对称仲裁协议是不对等?几乎每一个条文在我看来都是不对等的去保护银行。
更进一步,银行也有符合商业实践的合理合法的原因去坚持不对等管辖权条文。跨国银行传统上喜欢去伦敦或香港的法院,而不愿意去仲裁,因为他们面对的争议很多都是追偿债务的问题,法院针对偿还债务的争议往往是以简易判决就做出决定,既快捷又经济,在金融中心执行起来也容易。但是随着中国企业越来多的参与到国际金融市场,包括发行国际债券,国际银行作为债券的承销人或管理人,一旦债券发行人出现延迟支付利息或本金,国际银行担心去传统喜欢的伦敦或香港法院,将来判决书难以在中国内地执行[1]。反而是更喜欢选择仲裁,通过在中国内地执行仲裁裁决的方式来追偿债务。这可看出,银行有权去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或管辖法院是因为一旦有了如债务人欠债的争议,银行就可以衡量针对该特定债务人(法人或自然人)是否需要去中国内地执行,如果没有必要 (例如债务人在香港就有大量的资产),银行就可以选择香港法院了。在银行这样合法与合理的商业实践考虑与做法下,法院没有理由不去尊重当事人的约定,更不会只根据某条文对双方不持平,就去干预,这根本是否定订约自由和毁灭当事人的交易。
本来,法律认可双方自由选择解决争议方式。而这种不对称的仲裁协议只不过是仲裁协议的一个变形,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在普通法下不对称管辖条文的问题早已有之,也已经有定论,而不对称仲裁条文也适用同样的法理,并也有先例确认其有效性。那就是法院接受这是双方的订约自由,只要订得清楚明确,你情我愿,即使是不对称,也完全可以履行。
这可见英国 NB Three Shipping v Harebell Shipping [2004] EWHC 2001 (Comm);Law Debenture Trust Corp v Elektrim Finance BV & Ors [2005] EWHC 1412 (Ch);Barclays Bank plc v Ente Nazionale di Previdenza Ed Assistenza dei Medici Degli Odontoiatrie [2015] EWHC 2857 (Comm); Commerzbank AG v Pauline Shipping Limited Liquimar Tankers Management Inc [2017] EWHC 161 (Comm)(不对称管辖权条文)等先例
新加坡上诉法院案例:Dyna-Jet Pte Ltd v Wilson Taylor Asia Pacific Pte Ltd [2017] SGCA 32
问题中提到香港没有这方面的案例也不准确,例如在 China Railway (Hong Kong) Holdings Ltd v Chung Kin Holdings Co Ltd [2023] HKCFI 132先例中就出现了不对称仲裁条文。另香港也有确认不对称管辖权条文有效的案例,法理都是一样。这案例包括: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Asia)Ltd v Wisdom Top International Ltd [2020] HKCFI 322;Union Bank of India v Glory Universal Group Inc [2020] HKCFI 3057。
法国法院也认可这种不对称仲裁条文。不过世界范围来看,确实有国家的法院会拒绝承认这种不对称仲裁条文的效力,例如俄罗斯、土耳其,但这在我们看来,好像不同的执行地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执行会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并不是主流的看法。只是在实际业务涉及到时才需要去有针对性的了解。
接下来从仲裁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仲裁涉及仲裁地、仲裁执行地、仲裁条文适用法,会需要当事人和律师在订立这种不对称仲裁条文时考虑在仲裁地法、仲裁执行地法以及仲裁条文本身适用法下,涉及的不同的法院对此问题的看法,从而不会在将来开展仲裁或执行裁决书时带来风险。
综上,可见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合同法和仲裁结合与适用,而更为根本理念还是在合同法。
另外,据悉中国法下对这类条文存在一些争议,尤其是:(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争议可以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协议无效 ”,即“或裁或诉”的条文无效,因此过往有一些法院依赖此法律判一些不对称仲裁条文无效;(2)违背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但看来在近年来中国法院的态度也在改变与和国际主流做法接轨,包括(1)将不对称仲裁条文认为只是赋予当事人选择权,选择后就会确定,因此不属于“或裁或诉”的无效条文。其次是(2)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审判工作座谈会 》第一条第2款说:“2.【非对称管辖协议的效力认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签订的管辖协议明确约定一方当事人可以从一个以上国家的法院中选择某国提起诉讼,而另一方当事人仅能向个特定国家的法院中提起诉讼,当事人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该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管辖协议涉及消费者、劳动者权益或违反民事诉讼法专属管辖规定的除外。”本着同样的法理适用来看,也是不应再以不公平合理为由排除这类不对称仲裁条文了。这类判法可见北京金融法院( 2022 )京74民特4号民事裁定书。这种法律的变化也配合中国希望发展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

[1] 2019年1月18日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尚未生效。而目前适用的2006年签署的《关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据悉根据该安排去内地执行仍然存在非常多的困难与障碍,并且整个过程非常耗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