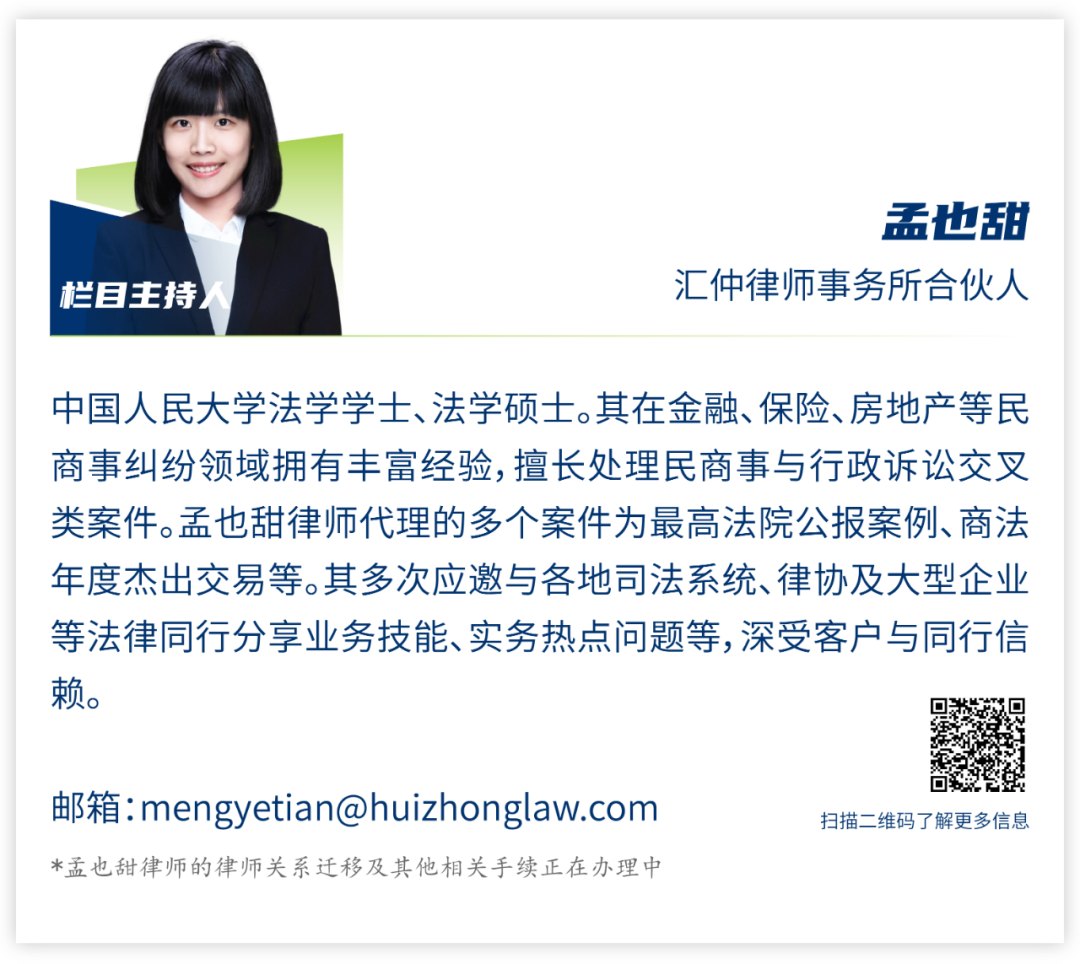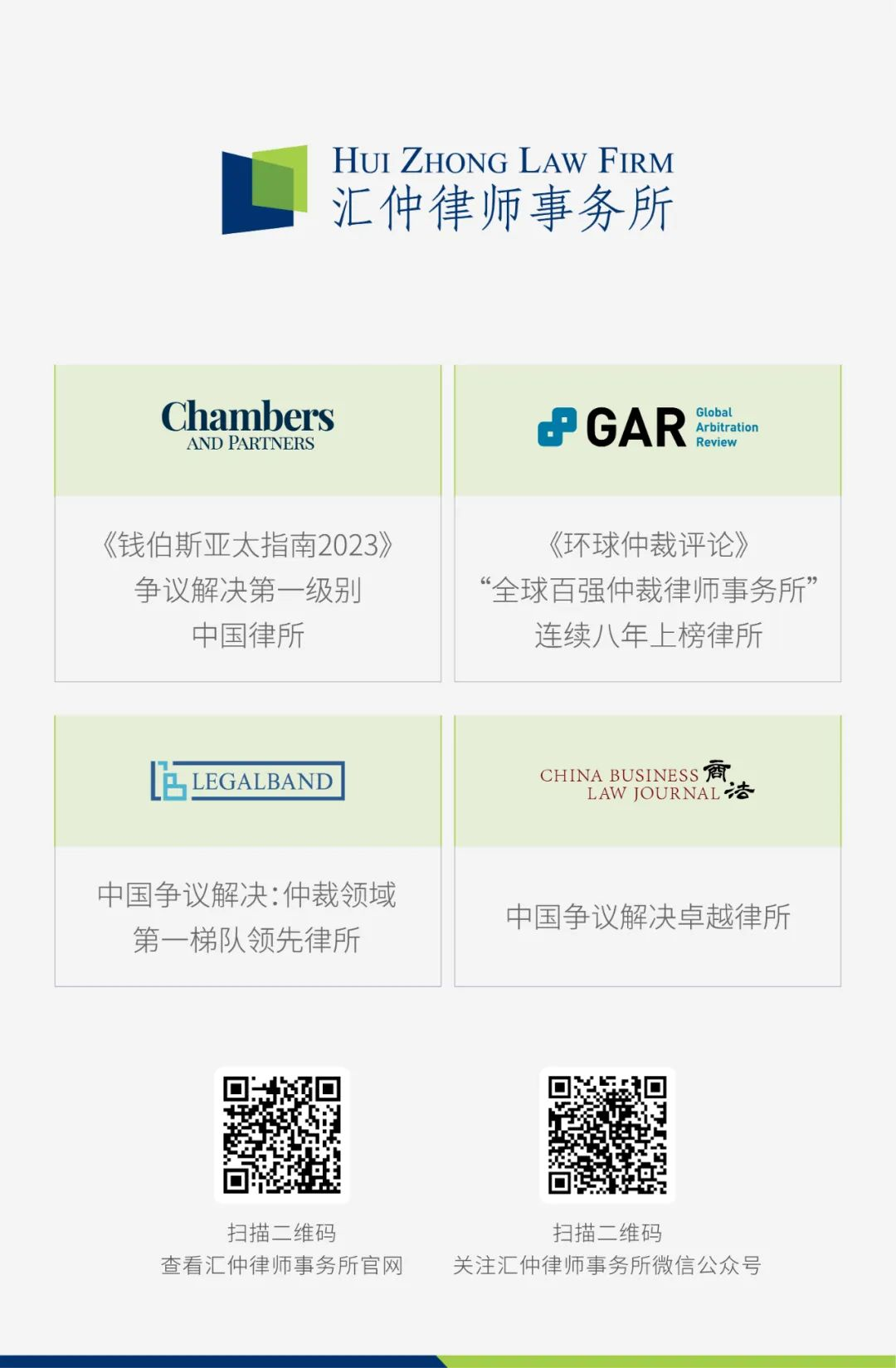那么股权转让纠纷中,如遇交易后标的公司业绩反转,受让方所称遭受“欺诈”该如何判断?以此为索引,本文将讨论在股权交易中假如出现财务数据问题,标的公司是否必然存在财务造假?转让方是否必然欺瞒相关事实?受让方是否因此陷入错误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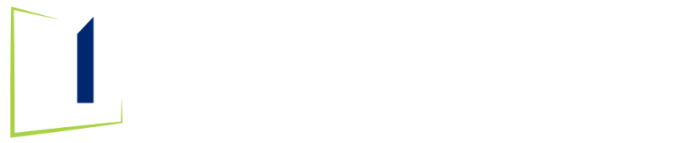
标的公司如果通过财务造假营造繁荣假象,交割后业绩很大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回落。然而,业绩回落并不能反向推导出标的公司隐瞒了真正的经营情况。
转让方:数据差异不等同财务造假
受让方一般会通过某一审计报告提出标的公司存在财务或业务数据不真实。此时,转让方可以分析所谓的问题是否与会计处理不规范、财务专业判断相关。会计处理不规范则一般是指行为人疏忽或误解造成的错误。如收入分摊期间不合理、费用没有在发生当月计提等。财务专业判断则涉及不同人士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对会计处理方法的个人见解。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和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为财务处理提供了一定酌情决定的范畴[1],任何人都可以坚持自己对处理规则的理解。而且,如果对某一项交易或事项,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有很多,如不同的资产折旧摊销方式,这些处理方法之间实际并无对错之分[2]。因会计处理不规范、财务专业判断产生的差异均不宜认定为财务造假[3]。
受让方:证明财务造假的直接证据
受让方在提出标的公司存在财务造假时需要直指核心。例如,标的公司现金无中生有,直接虚增银行存款;业务凭空捏造,以空壳公司扮演客户、供应商;债务弄虚作假,隐匿大额抽屉协议。掌握此类切实的证据,并通过审计报告、银行流水、纳税申报、公司现场经营状态等证据相互钩稽,方能让标的公司无从辩驳。相反,如果仅仅系理论上的推导,凭借某几个财务指标的异常、某存在争议的会计处理、自行统计的数据[4],或较难让法院直接认定标的公司存在财务造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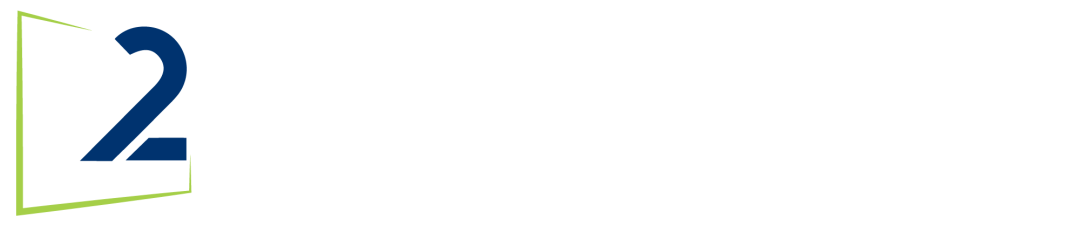
欺诈行为分为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具体到此类股权转让纠纷中,受让方主张欺诈的事实即是财务造假,因此需要在积极行为情形下考虑是否构成欺诈,即转让方是否明知存在财务造假,仍作为“真实”情况披露。
转让方:无法及无法知悉财务造假
对转让方而言,一旦标的公司确实存在财务造假,其作为收取交易对价的直接利益相关方,似乎难逃被认定为存在指挥造假的行为。但如果转让方系标的公司纯粹投资方或中小股东,或可通过证明自身无法及无法知悉财务造假,最终证明自身在股权交易中没有欺诈行为。
其一,转让方无法财务造假,如转让方不参与标的公司的日常经营,不掌握经营管理权和财务管理权。通常而言,标的公司可能向不掌权的股东提供的仅有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难以直接反映标的公司的具体运营情况,转让方能够向受让方披露的也仅限于报表信息[5]。在转让方既没有途径参与业务经营,也没有途径接触财务数据的情况下,遑论虚增业务粉饰财报。
其二,转让方无法知晓财务不实,如论证标的公司的财务造假手段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受让方在交易前的尽职调查、交易交割期内以及交易后一段时间的实际经营中均有机会发现标的公司存在财务造假,而其在这一相当长时间内亦未发现,难以要求纯粹投资方或中小股东(即转让方)在交易前即知晓或有能力知晓标的公司财务不实。
受让方:直接参与或明知存在造假
如上所言,即使标的公司存在财务造假,转让方仍存在否认其知悉欺诈事实的空间。因此,受让方仍需重视转让方直接参与或明知存在造假的证明,尽可能搜集转让方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材料。例如,转让方是否占有标的公司董事会多数席位、转让方是否有权任免标的公司重要职位、重大合同的签订是否可以体现转让方的参与过程。
退一步而言,转让方作为标的公司的股东,即便未参与经营,仍应当了解标的公司的业务情况。通常而言,并购交易中转让方会作出关于信息披露的承诺并签署相应文件,受让方可结合该承诺,主张转让方为促成交易的达成,在未核实具体信息内容的情况下向己方承诺信息真实,属于欺诈行为[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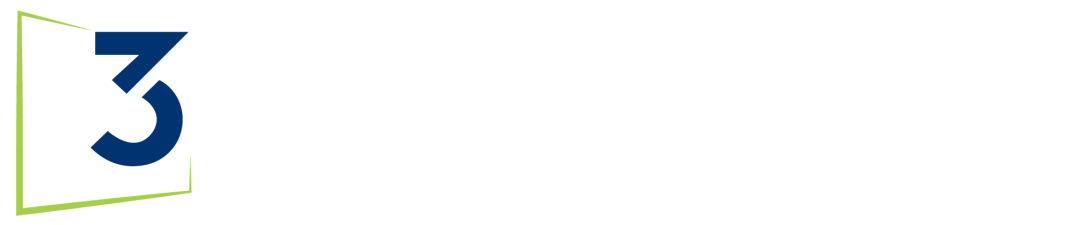
即使查明标的公司存在财务造假,根据欺诈的构成要件,还要求受让方因此陷入内心错误。股权转让纠纷中受让方所主张的“内心错误”一般是称其误信“标的公司未来具有良好的盈利空间”,并误以“虚高价格”受让标的公司。我们认为,判断受让方是否陷入内心错误,还需要通过双方义务、交易商业目的、股权实际价值等角度综合分析。
1. 双方是否已尽各自义务
转让方:受让方未尽审慎调查义务
受让方作为平等商事主体,在收购大额资产时负有审慎调查义务,应当通过合理途径对标的公司的各项状况审慎调查后,再作出是否受让股权的意思表示[7]。通俗来说,受让方不是没有任何风险识别能力的“傻白甜”。否则,如果允许受让方在尽调过程中无所作为,又允许其事后挑刺式的挖掘标的公司财务问题,继而无条件地要求转让方承担责任,那是赋予了股权受让方一个万能的挽回自身投资失败风险的投机渠道。
受让方:转让方未尽信息披露义务
转让方披露真实信息的义务不因受让方的审慎调查义务而免除。且受让方在并购交易中需要依赖转让方提供的信息作出决策,即使在交易前已经作出完整的尽职调查,仍是信息劣势方。特别是对于标的公司隐瞒债务风险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隐瞒巨额债务、未披露的对外担保、未缴税费及罚款、潜在的合同违约、潜在的其他未支付款项等等[8]。这些情况都难以在前期的尽职调查挖掘出来,甚至在受让方实际经营时都难以发现,风险往往直至第三方要求标的公司归还借款、承担付款责任时方才爆发。转让方隐瞒或拒绝提供某一材料的行为很可能导致受让方误信标的公司的表面经营状态。因此,即使该等事宜在期后爆发,法院仍有可能因此撤销股权转让合同[9]。
特别提示受让方的是,受让方在办理交割手续时,不仅仅要注意标的公司公章或重要合同,还要应当逐一梳理标的公司全部移交材料。假设能够证明标的公司的债务情况的文件夹杂在移交的材料中,法院反而有可能认为转让方已尽披露义务[10]。
2. 判断交易核心商业目的
转让方:财务数据并非受让方决定收购的唯一依据
持有该观点典型案例如(2020)最高法民终918号,案例中转让方隐瞒了标的公司的部分债务。最高法院认为,该行为是否足以导致受让方作出错误意思表示,应结合股权转让的签订背景,合同的相关条款,以及合同履行情况综合判断。例如,受让方开展并购交易,有可能是基于对某一项目开发前景的判断,有可能是为了补强自身某一板块的短板,也有可能是谋求某一领域的全部份额。彼时,交易本就包含复杂因素。受让方关注的本就不仅仅在于部分财务数据是否漂亮,单凭财务数据不足以受让方作出是否收购的决定。
受让方:公司的盈利能力系受让方决定收购的原因
持有该观点典型案例如天山生物(300313)收购大象股份的纠纷[(2020)新民终138号],案例中双方明确约定了受让方的收购目的即“收购优质资产,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最高法院最终据此认为,受让方系基于标的公司是一家盈利企业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当然,该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交易目的。更多时候协议中可能未就目的作出明确约定。此时,司法或仍然认为标的公司能否实现盈利属于商业风险,其与公司股权转让时情况和嗣后受让方经营行为、市场环境等密切相关。客观上标的公司是否能达到预期盈利,或较难构成受让方陷入内心错误的理由。因此,也提示受让方可以在此后交易中选择将交易目的明确写入转让协议中。
3. 股权交易价格的判断
转让方:股权价格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对于交易双方而言,股权转让价格是商事主体的“主观”判断[11]。股权价格包含公司投入、经营、财务状况,市场前景,技术水平等复杂因素[12],其价值之估算及其未来的变化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故股权价值的高低不能简单地或静态地通过财务数据来确定。
受让方:造假行为实质影响交易对价
标的公司的造假行为正是为了抬高其交易对价。如果标的公司的业务状态并不如预期,受让方则并不会以原有对价完成此项交易。股权价格固然受多种因素影响,但一个年利润为100万的公司股权价值,当然不能与年利润1000万的同日而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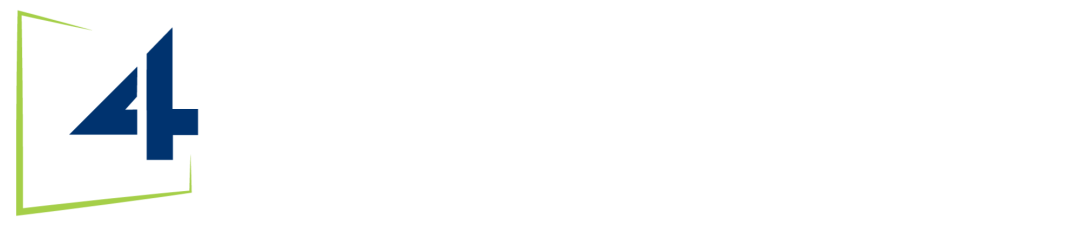
合同是否必然会被撤销?
最后,司法裁判也是该纠纷中角力的一环。即使标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存在一定问题,裁判者还需考虑撤销合同是否系恰当的救济手段。股权交易不同于一般的货物买卖交易,股权作为标的资产兼具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属性。股权交易后,标的公司控制权和经营管理权转移给了受让方。假若受让人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效行使了股东权利,主导了标的公司的经营管理,相较股权转让前,标的公司也相应产生了诸多改变。若此时撤销股权转让合同,其后果及后续处理则相当复杂,甚至还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法律争议。涉及包括如何返还交易标的、如何作价或如何评估受让方的经营管理活动给标的公司价值所带来的溢损影响、如何分配各方利息归属,划分各方责任等问题,不利于维护交易和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也很可能影响其他相关方的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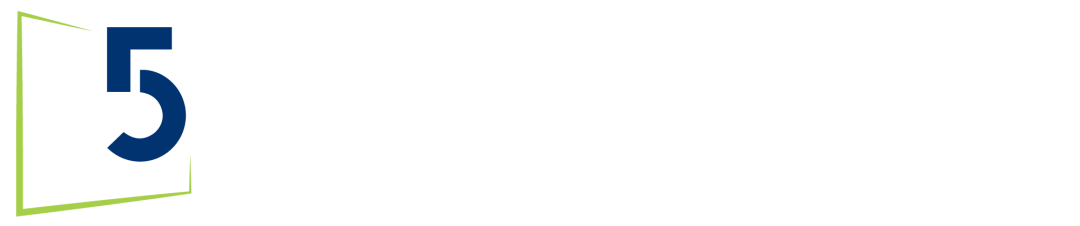
小结
商事关系的本质乃是资本的营利活动。在理论假设上,商主体是具备相应知识、经验、资质的理性“经济人”[13]。司法审判一般会更加维护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审慎处理因欺诈而要求撤销合同的诉请。股权转让协议是否能因欺诈而撤销仍然是一场各方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