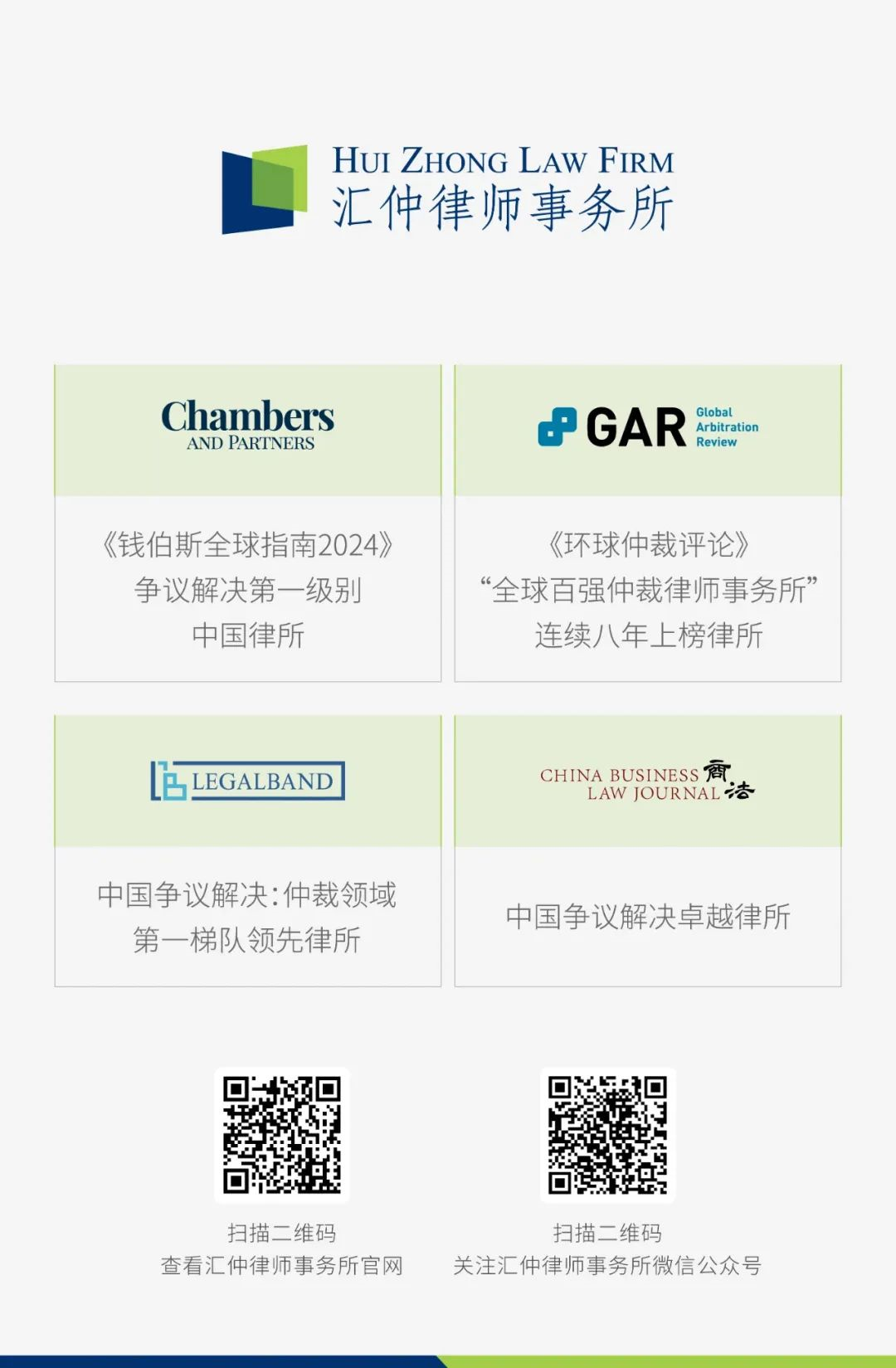文|朱瑶瑶
文|朱瑶瑶
引言:
承上篇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对赌纠纷中的适用,下篇梳理了政策和法律规范变化、政府行为、价格涨跌在此类案件中对不可抗力规则或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情况。大部分案例未予支持,除上篇讨论的因果关系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裁判机构认为该等事由属于商业风险。基于此,本文将聚焦此类案件中商业风险与不可抗力、情势变更的判断标准,以期为当事人在对赌纠纷中如何进行主张提供参考。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指出“商业风险属于从事商业活动的固有风险,诸如尚未达到异常变动程度的供求关系变化、价格涨跌等。”对于商业风险与非商业风险的识别,最高法院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明确,最核心的标准是个案的重大变化是否符合具体行业领域内的商事规律,市场主体对此是否具有可预见性[1]。不同商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对于风险认知不同,故需要具体到个案判断变化是否符合商事交易规律,进而判断是否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或情势变更制度。基于此,笔者以近年对赌纠纷中涉及的政策和法律规范变化、政府行为、价格涨跌为例,具体到各行业,探索政策变化体现的商事交易规律,分析具体行政行为背后的宏观政策背景,进而总结裁判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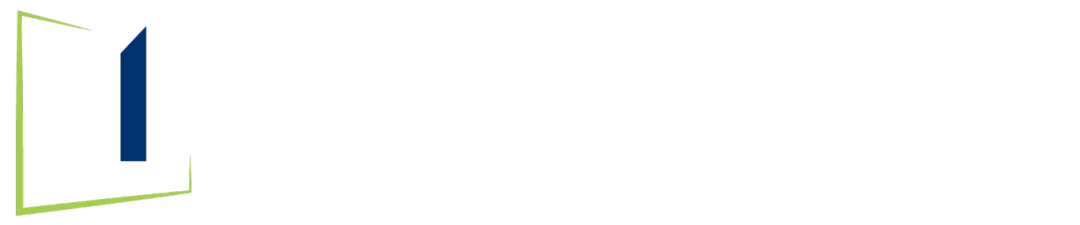
政策和法律规范变化
政策调整和法律规范变化被认定为商业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变化具有一致性、连贯性、科学性、规律性,符合此前政策精神和指引,或已被广泛讨论、知悉,是行业从业者可以预见的。但是,如行业政策或国际形势发生突发性、根本性的变化,对于当事方造成直接、重大影响,则可能被认定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下文笔者将以涉对赌案件中涉及的法规和政策变化为例,具体说明上述司法裁判思路。
(一)符合监管趋势的政策变化
行业监管政策的变化是对赌义务方的常见抗辩理由。但是,行业监管政策的变化通常不是一蹴而就,往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连贯性和规律性。例如,主管部门可能一直持审慎态度,早期已陆续发布加强监管或收紧政策的通知、文件等,或者早已反映在宏观调控政策中,故该等政策不具有突发性,是行业从业者可以预见的。再者,加强监管的政策出台常为规范和整治行业乱象,也属于行业从业者依法合规经营应具有的必要认识。基于此,相当数量的涉对赌纠纷案件中,裁判机构认为符合监管趋势的政策变化不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1.严控互联网销售彩票
在北京高院(2021)京民终178号案中,义务方主张财政部等八部门于2015年和2016年发布公告和通知,全面禁止互联网销售彩票,导致目标公司主营业务彻底处于停滞,故未能按约上市的原因是国家政策突变的不可抗力造成,其无需回购股权。经检索,从2007年到2015年,虽然互联网彩票销售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监管部门始终持谨慎态度,通过多次政策调整和市场整顿,严格控制互联网彩票销售,甚至于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多次叫停网售彩票。可见,加强监管审批甚至叫停互联网销售彩票是监管部门的一贯政策精神,而义务方所主张的政策变化符合该趋势。故两审法院认定作为互联网销售彩票的经营者应当有所预期,上述政策变化不属于不可抗力。
2.收紧互联网金融监管
在上海嘉定法院(2022)沪0114民初861号案中,义务方主张目标公司属于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行业,案涉协议签订后该行业的监管政策发生了由松到紧的根本性、突发性变化,导致目标公司业务大幅下降,难以推进上市计划,应当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撤销回购条款。在广州中院(2022)粤01民终12658号案中,义务方同样主张P2P业务金融监管政策突然变化属于不可抗力。经检索,2015年,互联网金融风险事件频发,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并着手整治,互联网金融正式进入监管年;2016年,监管部门出台了多项政策,规范各类互联网金融业态;2017年,被称为“史上最严”金融监管年,监管层发布《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指引》《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信息披露指引》等政策,加速行业的合规步伐。可见,2015年至2022年期间,监管部门系逐步强化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义务方所主张的政策变化并非突发,具有一定连贯性。且作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商事主体对需依法合规开展应具有必要认识,就监管政策收紧带来的可能影响也应具有一定预见能力。因此,两案判决均未支持义务方的上述主张。
3.强化影视行业监管
在深圳罗湖法院(2020)粤0303民初16233号案中,义务方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业绩对赌协议,主要理由为协议于2018年签订后,相关部门加强对影视行业的监管,加强税收监管,规范明星片酬过高问题,导致影视剧发行不如预期,目标公司收入大幅下降。经检索,近年来影视行业的监管政策持续加强,其中2018年至2019年间,影视行业经历了多项政策整顿,主管部门颁布多项指导意见对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进行治理,对影视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但是,该等政策变化既是守法经营的应有之义,也符合主管部门逐步强化监管的态度,如广电总局早于2017年已开始对电视剧题材、质量、演员片酬以及收视率数据等问题实行强监管。故法院认为“政策因素应是其在经营中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且各行业在经营中都应当守法经营,加强行业监管不属于无法预见的事件。”另在某仲裁案件中,义务方主张国家政策及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导致电影无法过审和上映,构成不可抗力。仲裁机构与上述案件观点一致,“涉及黄赌毒、血腥暴力等情节的电影难以过审是我国电影界众所周知的;因存在策划、拍摄、制作方面的问题而不符合上映的监管要求从而使得电影无法如期上映的情形,应当属于可以预见的商业风险。”[2]
4.暂停或收紧IPO审核
证监部门暂停IPO审核是上市对赌纠纷中最常见的抗辩理由。在广东高院(2017)粤民终859号案中,义务方提交了从网上下载的有关证监会8次停止IPO的资料,主张证监会暂停新股发行构成不可抗力。珠海香洲法院(2015)珠香法民二初字第1893号案、新疆阿克苏中院(2015)阿中民二初字第112号案中也存在类似抗辩。经检索,1994年至2015年期间,监管部门曾九次暂停IPO审核,短则3个月、长则15个月。对赌当事方作为拟上市或已上市的公司的控股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相关主体,应完全能够预见到暂停IPO发行的可能。故上述案件中,法院均认定IPO审核政策变化属于合理的商业风险。
阶段性收紧IPO政策也是此类案件中常见的抗辩理由之一。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19)沪0115民初23587号案中,义务方指出此前IPO成功的案例数量和概率均较高,而2018年大幅下降且上会审核更加严格,属于情势变更。法院对此认定“互联网文化领域公司IPO情况的变化属于合理的商业风险”。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监管部门通过提高审核标准、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加大现场检查力度等方式从严审核上市申请是必然趋势,证券市场相关主体应有所预期。因此,司法实践倾向认为暂停或收紧IPO审核属于商业风险。
(二)具有科学性、规律性、连贯性的产业政策变化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往往具有科学性及规律性,制定者会进行反复研究论证,以保证符合特定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及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产业从业者可以预见的。同时,产业政策的调整通常贯穿整个产业发展周期,当事人签订协议及履约都处于产业政策的调控之下,遇到政策调整的概率较高,其也应当有所预见[3]。因此,司法实践通常认为具有科学性、规律性、连贯性的产业调控政策属商业风险。以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棉花产业和新能源汽车补贴及煤改气政策变化为例:
1.棉花产业补贴政策调整
某仲裁案件中,义务方抗辩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导致补贴减少,造成目标公司主营的棉花育苗销售业务收缩,销售区域的棉花种植面积急剧减少,进而导致未实现的经营业绩和上市计划,应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免除回购责任[4]。案涉期间棉花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变化为:2011年之前,棉价处于大幅波动状态。2011年,为了稳定棉价,政府开始实施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以固定价格收购棉花。随着棉花产能过剩,国外市场需求降低,国内棉价因临时收储政策保持高位,造成了国内外棉价严重背离。为了国内棉价回归正常的市场供需关系,政府于2014年开始实施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取消临时收储政策。可见,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符合产业发展的客观实际,也符合产业市场化的一般规律。且自20世纪90年代起,国家确立了棉纺织业向西迁移的方针,以提高新疆棉花的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故其他地区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呈缩减趋势。而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改革政策以新疆为试点正是该宏观政策连贯性的体现。因此,该政策具有科学性、规律性、连贯性,仲裁机构认为棉花产业从业者对此应当有合理预见,不属于不可抗力。[5]
2.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取消
在合肥中院(2021)皖01民终3938号案中,对赌义务人主张目标公司未能在2017年12月31日前被上市公司收购的原因是“新能源车的国家补贴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国家补贴标准逐年降低,至2020年国家的政策补贴被取消”,应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免于支付收益款。新能源汽车的国家补贴政策主要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2010年,政府推出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推动产业的起步和发展;至2016年,为推动产业市场化和自主发展,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推出更多高续航的车型,补贴政策引入了退坡机制,逐年减少补贴力度;至2022年,主管部门发布通知,明确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将于2022年12月31日终止。可见,新能源汽车的国家补贴政策变化符合市场化的需求和宏观调控的一般规律,该补贴政策是逐步退出,具有连贯性,属商业风险。该案中,法院持相同观点,认为“新能源车的国家补贴标准逐年降低应系中航公司自身经营的正常外部商业风险,且该补贴政策并不是2017年就被取消的,到2020年才被取消”,进而未采信义务方的抗辩。
3.“煤改气”政策加速推进
在北京高院(2020)京民终677号案中,义务方主张2017年底国家开始推行“煤改气”政策,致使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进而导致承诺业绩无法完成,属于情势变更。“煤改气”工程早在1997年已经开始探索并制定相关政策。随着大气污染的加剧,国务院于2013年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强调能源转型升级方向,“煤改气”相关政策逐渐受到重视。2016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特别强调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的问题,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因此,《关于北方重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煤改气”气源保障总体方案》的出台是延续上述计划和贯彻会议精神,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法院据此认为,义务方作为专业的城市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知晓“煤改气”工程的相关政策,对于国家加大“煤改气”力度导致天然气需求激增,甚至出现全国性的供气短缺、天然气价格大幅提升应有预期,故“煤改气”政策的发布属于固有的商业风险。
(三)已广泛征求意见的法规变化
法律法规的出台通常需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发布前往往已在相关领域或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并充分讨论,产业从业者应可以合理预见[6]。因此,已发布征求意见稿或充分讨论的法规或政策变化通常不被认定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某仲裁案件中,对赌义务方主张《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出台导致目标公司不再具备开展项目的相关资质,进而导致目标公司未于2019年12月31日上市,故应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免于承担回购义务。《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系于2016年5月审议通过,2016年9月发布征求意见稿、2016年12月正式发布、2017年7月实施,故其发布前已引起业界广泛讨论和关注。仲裁机构认为案涉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于2015年6月签订,目标公司作为一家从事证券期货投资产品销售或服务的金融服务公司,应对行业政策较为关注并相对敏感,故《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出台与实施能否被认定在签订协议时无法预见值得商榷。且2016年5月出台后,义务方也有足够的时间按照该办法的要求对公司经营与项目运作进行有效调整,并非不可克服,故该办法出台不构成不可抗力[7]。
(四)根本性的政策变化
虽然监管政策通常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但如监管政策发生根本性、颠覆性的变化,远超行业从业者的预期,导致目标公司彻底无法经营或无法上市,法院可能会认定该政策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以教育行业双减政策为例,法院对其是否属于商业风险存在不同认定。
2021年7月24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政策)的发布对校外培训机构及教育相关公司造成影响较大,部分机构业务规模缩减、业绩大幅下跌,甚至直接关停。其要求从严审批机构、严禁资本化运作、严控学科类培训机构开班时间等,主要措施包括:(1)针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各地不再审批新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2)针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严格审批、依法监管。
教育行业的对赌纠纷案件随之增多,对赌义务方常引用双减政策主张适用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免于承担股权回购或业绩补偿等责任。例如,在宁波中院(2022)浙02民终4311号案中,义务方以“双减政策导致睿易公司无法顺利开展相关业务,从而导致睿易公司无法顺利上市”为由主张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在北京一中院(2022)京01民终9639号案中,义务方主张双减政策导致目标公司业绩下滑,不具有上市条件,构成情势变更;乌鲁木齐米东法院(2021)新0109民初9193号案、北京一中院(2023)京01民终12159号案、北京金融法院(2022)京74民初207号也存在类似抗辩。经检索,双减政策颁布前,主管部门已于2014年发布《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于2018年发布《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逐步加强对校外教育培训的监管。如上文分析,作为专业的培训机构,对主管部门将进一步收紧政策应有一定的敏感性和预见可能性。上述案件中,法院因此认为双减政策属商业风险。
但是,笔者认为双减政策与加强监管的政策存在不同,其对含有学科类培训范围的机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不再审批”“改为非营利性机构”、严控培训时间等规定将直接导致含有学科类培训业务范围的机构招生数量减少、场地空置、教育资源闲置等。例如,在南昌青山湖法院(2022)赣0111民初236号案中,法院认为双减政策的出台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故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在沈阳皇姑区法院(2021)辽0105民初12069号中,法院认为“该政策对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而言应当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原告因该政策第13条而无法申请办理有关办学许可”,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合同。在珠海斗门区法院(2022)粤0403民初1777号案中,法院同样认为“国家于2021年出台双减政策,其施行力度较大、准备期较短,系原被告双方在案涉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已经超过了一般商业风险的范畴,造成了原告的外部经营制度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可认定为情势变更。”虽然该等案件案由属于租赁合同纠纷,但是对在其他民商事案件中判断双减政策是否为商业风险具有参考意义。如目标公司的主营范围包括学科类培训,其很可能将因该政策无法推进上市工作,或因不得新设培训机构和缩短经营时间等,业绩大幅下滑,无法达成承诺业绩。在此情况下,法院可能将综合其他构成要件认定双减政策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
(五)国际局势动荡导致的政策变化
国际形势变化也是对赌义务方常见的抗辩理由,如因中美贸易战而导致的美国加征关税、交易对手方受到美欧经济制裁等。部分对赌案件认为这属于商业风险,例如在宁波中院(2021)浙02民终4423号案中,法院认为美国加征关税属于商业风险,且无证据证明其对目标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但是,如国际局势发生剧烈、突发的变化,法院也很有可能认定相关政策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例如,在某仲裁案件中,申请人提出美国对中国借壳上市公司进行针对性关注和阻击,导致无法按照《上市及投融资合同》约定赴美挂牌上市,请求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该合同。仲裁机构认为,美国相关机构对中国概念股的针对性阻击,并非一般商业风险,而是其在发现个别中国借壳上市公司存在财务造假行为后,对全部中国概念股的针对性检查和排斥,其已导致数家中国企业退市或放弃赴美上市,这属于美国金融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支持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解除合同。[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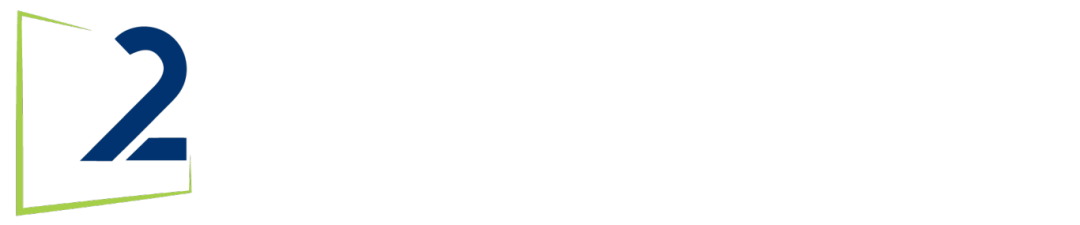
政府行为
对赌实务中,行政执法、行政征收、政府合作、贸易救济手段等政府行为也是义务方主张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或不可抗力规则的常见理由。政府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上文已讨论前者,而后者司法实践较少认可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例如,在(2021)最高法民申6537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政府行为“应限于政府为了应对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社会事件等作出的具有宏观性应对措施,或者针对社会经济生活作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政策调整等。如果政府出于一般社会管理需要,就社会生活中某一具体的事项作出的具体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影响的宏观性和全局性,在合同法领域则不能将该政府行为定性为不可抗力,而应属于商业风险的范畴。”再如,北京三中院在(2019)京03民终2112号案认为“具体行政行为出现的次数太过频繁,如果一概把具体行政行为列为不可抗力,容易导致不可抗力制度的滥用,从而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某些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程序撤销。所以,并非所有具体行政行为均为不可抗力。”下文笔者将以行政执法、行政征收、政府合作、贸易救济手段为例,具体说明上述司法裁判思路和观点。
(一)行政执法
目标公司经营过程中因环境、安全等问题被处以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等措施,进而影响经营业绩或阻碍上市进程,裁判机构倾向认为合法合规经营是市场主体基本义务,行政执法行为属于商事主体应当预见违法违规后的风险。在北京三中院(2021)京03民终6518号案及该案再审北京高院(2021)京民申8065号案中,对赌义务方主张在目标公司“没有环保违法行为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因园区环境质量较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及‘12.9’重大爆炸事故,要求园区全部企业停产,属于不可抗力。”法院未予支持原因包括“保护生态环境、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是当前我国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亦为政府在行政管理及执法中的一贯要求,目标公司作为主要经营农药生产及其他化工产品销售的企业,理应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及自身存在的环保问题知晓并预见,并应积极采取整改措施”,故“停产”要求不属于不可抗力。
反复多次实施的政府行为也较难被认定为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在保定中院(2020)冀06民终2610号案中,对赌义务方主张“北魏镇人民政府要求鑫磊公司实施错峰生产及因天气问题而停产属于不可抗力”。经检索,《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据重污染天气的预警等级,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应急需要可以采取责令有关企业停产或者限产……”近年来,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据此实施“秋冬季错峰生产及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停限产”政策也屡见不鲜。故法院认为“在已经存在因天气污染限产的情况下,普通人应该能够预见政府的应急响应措施会造成停工”,不适用不可抗力规则。
(二)行政征收
司法实践对于行政征收是否构成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存在不同观点,通常需结合个案具体情况,判断当事方对该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预见性及其对合同履行是否造成重大影响。例如,在江西高院(2015)赣民一初字第3号案中,投资资金本约定专用于南昌宝葫芦三期项目建设,但因政府强制征收导致该项目无法启动,触发回购条款。法院认为目标公司土地被政府征收构成不可抗力,目标公司无需承担未按照约定利率进行分红的违约责任。另基于合同相对性,该行为不构成义务方履行回购义务的不可抗力,但鉴于实际情况,政府征收导致义务方在投资不到一个月即面临回购133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的巨大压力,故免除义务方的违约责任。可见,法院主要是考虑到行政征收对合同履行造成了直接、根本的影响,才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免除责任。而在最高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1277号案中,义务方主张“系因政府违背拆迁承诺,引发当地村民冲击药兴公司,进而导致该公司无法继续正常生产经营以及业绩不达标”。法院认为义务方“作为药品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在周围村民尚未搬迁的情况下就建厂投产,应当预见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纠纷的风险并应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故不构成不可抗力。
(三)政府合作
政府机关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与目标公司合作中产生的变故,可能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例如,北京二中院(2020)京02民终1581号案中,对赌义务方主张由于目标公司的主要项目是与各省市食药监局合作,但2017年至2018年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进工商局、质监局、食药监局三局合一的部门整合,其合作被暂停,导致目标公司未达承诺业绩,应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但法院认为政府部门机构调整具有可预见性,系商业风险。再如,贵州中院(2017)黔01民初596号案中,义务方主张区政府要求变更项目选址并紧急叫停项目合作,进而导致回购条件的触发,应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但法院认为这属于商业风险,义务方作为项目投资人,在充分了解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后应当知晓。
但在政府合作类案件中,行政机关与民事主体对政策调整或行政行为是否能够预见认定标准并不完全一致。因为行政机关的职权、专业和行政程序等因素决定行政机关作为公方当事人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私方当事人对于政府行为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故应当建立行政机关的专业标准和私方当事人的一般人标准的双重标准体系。对行政机关提出政府行为作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事由,法院应综合考量政策变化、规划变更等政府行为中行政机关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能力,对行政机关采用严格审查的标准[9]。
(四)国际贸易救济措施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发展陷入低迷,各种新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欧盟等多个国家或地区针对中国的多种产品发起了七十多起“双反”调查或采取其他经济制裁措施,导致贸易公司经营业绩直线下滑,而该等贸易救济措施也成为了涉对赌纠纷案件中的常见抗辩理由之一。国际贸易救济措施通常被认定为正常的商业风险,因为该等措施是为了恢复正常的进口秩序和公平的贸易环境,保护国内产业合法利益而被制定、认可,并可实施的贸易政策,市场主体可以且应当预见。
以“双反”调查为例,当进口产品以倾销价格或在接受出口国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低价进入国内市场,并对生产同类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成员方使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措施。厦门中院(2014)厦民初字第137号案中,义务方主张未达目标业绩的原因是“欧美对华光伏产业实行反补贴、反倾销策略,致使旭阳雷迪公司在2011年度多晶硅产品、太阳能电池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遭受重创”,应适用情势变更制度调整补偿义务。法院持上述观点并认为:“作为一国的贸易保护措施,进口国对出口国产品进行双反调查并非不可预见的情形,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在温州中院(2016)浙03民终660号案中,义务方同样提出类似抗辩,法院也认为“光伏产业遭遇反倾销反补贴政策及相关制裁措施虽非普遍现象,但亦属能够预见的市场风险,且并非直接影响乐园公司,不会必然导致乐园公司无法按期上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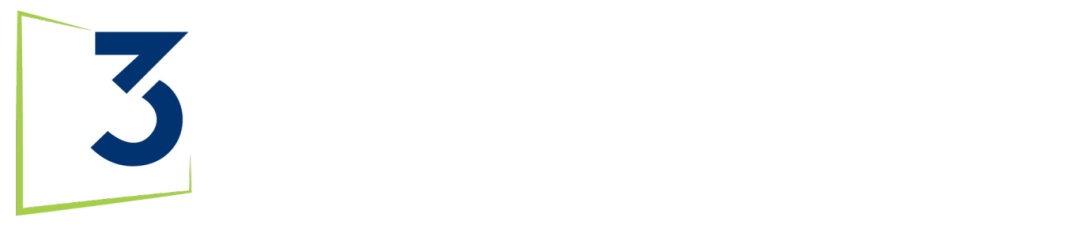
价格涨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二条及其理解与适用,交易价格的波动通常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但如因政策调整或市场供求关系异常变动等原因导致价格异常涨跌,超出了当事人订立合同时的预见能力,并导致了显失公平后果,才属于情势变更事由。对赌案件中,裁判机构常以价格涨跌未达到异常或未超过当事方的预见为由认定其属于商业风险。
例如,在广州中院(2023)粤01民终23949号案中,对赌义务方主张目标公司主营业务废物处理价格大幅下降,即普通危废物、含铜危废物处理价格降价幅度分别为86%、100%,此种降价幅度不合常理、无法预测,应属于情势变更;然法院并未采信并认为上述价格波动属于正常市场风险。在北京三中院(2021)京03民终6518号案中,对赌义务方主张目标公司2016至2018年业绩未完成主要原因包括其所主营的草氨磷价格大幅度下跌,法院亦未采信并认为“原料价格变化本身即是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会面临和应解决的问题”,且目标公司“除了经营草氨磷外,还从事其他农药生产销售等业务”,不能说明承诺业绩与草氨磷价格之间的直接联系。在长沙中院(2019)湘01民初313号案中,义务方主张“长沙县政府对涉案长沙县开慧镇养老项目一期土地平均地价确定为69.3万元/亩,超出签订涉案股权转让协议时预测的供地价30万元/亩”,土地挂牌价格较大幅度的上涨构成情势变更。法院未予认可并指出“地价大幅度上涨虽然可能超出当事人的预见,但在土地挂牌出让前,土地价格的变化仍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在上海一中院(2015)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712号案中,法院认为虽然超硅公司与陈猛证明了2012年超硅公司主营的蓝宝石衬底行业,市场价格暴跌,竞争激烈,超硅公司业绩未达到协议约定目标,显然与此相关,但该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状况应属于行业经营性风险,并不符合情势变更要件,故对陈猛关于约定业绩未达到系因情势变更的答辩意见,不予采信。
注释
作者介绍

朱瑶瑶律师 深圳
朱瑶瑶律师曾参与投资并购和证券发行等交易,富有公司合并、股权收购、首次公开发行等非诉经验;后专注于金融诉讼及仲裁领域内的理论与实务研究,为多家金融机构、国企及大型民营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律意见书等服务,并成功办理十数起疑难、复杂的重大民商事争议解决案件,为客户挽回数十亿元损失。
zhuyaoyao@huizhonglaw.com
+86 13544229505
声明: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可视为汇仲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或需要法律意见,请与本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