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后的《仲裁法》已由立法机关正式发布,并将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相比《征求意见稿》,正式条文对现有制度调整幅度较小,彰显“稳健”特征。依执行视角观之,虽修改内容有限,但影响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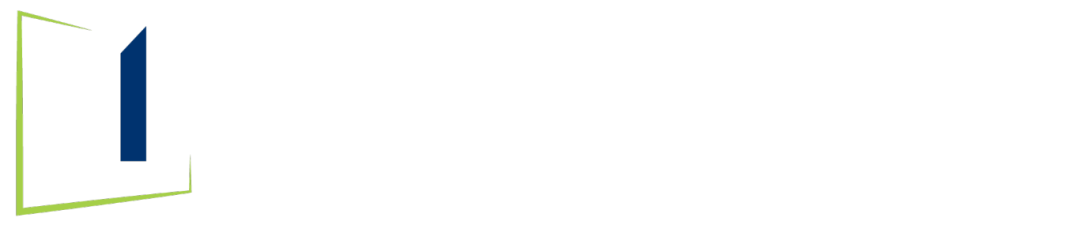
关于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级别管辖
(一)法律层面:付之阙如
自1994年起,《仲裁法》均明确规定仲裁裁决的执行管辖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2025年修订时,也仅有表述调整,即将原第62条的“民事诉讼法”调整为现第75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但是,《民诉法》仅规定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地域管辖,即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35条第2款),对级别管辖则付之阙如。实践中,关于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级别管辖的争议,从三部司法解释的内容变化可窥一斑。
(二)司法解释层面:两次调整
1998年《执行工作规定》第10条第2款规定,国内仲裁裁决参照各地法院受理诉讼案件级别管辖的标准确定。据此,标的金额较小的执行案件应当由基层法院管辖;大标的额的案件才由中级法院管辖。
2006年《仲裁法解释》第29条则明确仲裁裁决执行案件应由中级人民法院统一管辖,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缓解撤裁案件和不予执行案件的审级冲突。详言之,撤裁案件根据《仲裁法》由中级法院管辖,如果中级法院驳回了撤裁的申请,后续执行中,当事人又向作为执行法院的基层法院提出不予执行,基层法院有可能会根据民诉法裁定不予执行,从而产生上下级法院的审级冲突。而统一由中级法院管辖,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二是根据标的额确定管辖,大部分国内仲裁裁决将由基层法院管辖,“执行的法院级别过低,存在执行质量不高的问题”。
2018年《仲裁裁决执行规定》起草时,不少观点认为仲裁裁决执行与一般执行案件没有区别,没有必要全部由中级法院管辖。特别是小额网贷仲裁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严重挤占了执行资源。但也有部分直辖市法院同志认为,直辖市的中级法院不承担对下管理职能,仅承担办案任务,仲裁裁决执行案件在中院执行案件中占比很大,如果将全部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可能会导致中级法院执行案件不饱和。最终,《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2条延续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的规则,但增加了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执行的规定:若根据《执行工作规定》第10条,某一执行案件可以由基层法院管辖,该案件就可以指定给该基层法院执行。
(三)本次修订后:司法解释仍有调整空间和必要
如前所述,《仲裁法》本身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的管辖转引至民诉法,而民诉法对于级别管辖未作规定,给司法解释留下了充分调整空间。
就目前情况来看,2006年《仲裁法解释》将仲裁裁决的执行管辖统一到中级法院管辖的理由,恐怕已难以成立,考虑到实践中小标的仲裁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为更好的配置执行资源,应恢复1998年《执行工作规定》按照标的金额确定级别管辖的规则。
第一,《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20条明确规定,撤裁申请被驳回后,当事人再申请不予执行的,法院不予支持。并且,当事人同时申请撤裁和不予执行的,撤裁程序优先审查。《仲裁裁决执行规定》第2条第3款进一步规定,即便执行案件由基层法院执行,不予执行依然由中级法院审查。上述规定,已经解决了由基层法院执行仲裁裁决可能导致的撤裁和不予执行的审级冲突。
第二,基层法院执行水平较低的判断,本身可能就不是事实。实际上,由于基层法院执行实施案件更多,相比上级法院,可能对相关程序更为熟悉。如果属实,由中级法院统一执行仲裁裁决执行案件,就构成一种对仲裁裁决的“优待”。同样作为执行依据,何以仲裁裁决就应当获得比法院判决、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等执行依据更优的待遇,正当性颇值商榷。
第三,如果仲裁裁决执行案件按照标的金额确定管辖,确实导致部分中级法院执行案件不饱和。这部分法院也可以通过将其辖区基层法院不易处理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提级执行,解决自身“无案可办”的问题。
第四,2018年之后,不少中院已经将仲裁案件批量指定基层法院办理,并实践至今,未见明显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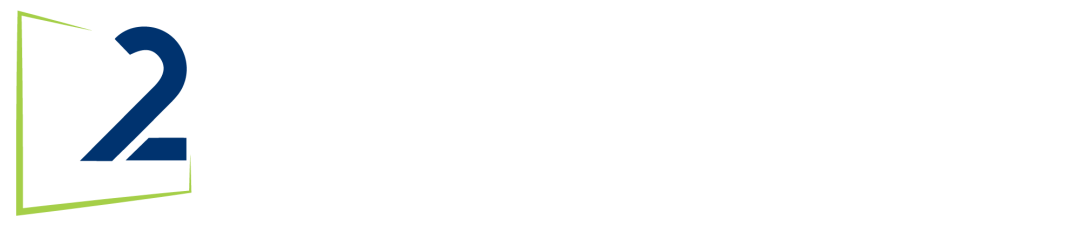
仲裁保全进一步完善
本次修订中,对仲裁保全制度做了如下调整:
(一)明确仲裁保全包括行为保全
相比原《仲裁法》第28条,修订后的《仲裁法》第39条,将仲裁保全从财产保全扩大至行为保全,即可以“请求责令另一方当事人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
(二)表明法院应当依法保全的态度
修订后的《仲裁法》第39条第1款,新增仲裁机构向人民法院提交保全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处理”的表述。
该句本来是法律应有之义,要通过立法再次强调,实际上意味着仲裁保全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虽然规范本身不能保障实际操作,但立法机关借仲裁法的修订强调仲裁保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办理,依然表明了其对该问题的态度,体现了对仲裁的支持。
(三)“新增”仲裁前保全
相比原《仲裁法》第28条,修订后的《仲裁法》第39条第2款新增了仲裁前保全的内容。
但实际上,《民诉法》自2012年就规定了仲裁前保全制度(2012年第101条)。只是实际中有的法院并未依法处理。
故与第39条第1款强调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处理仲裁保全申请一样,仲裁前保全在《仲裁法》中的新增更多还是表明支持仲裁的一种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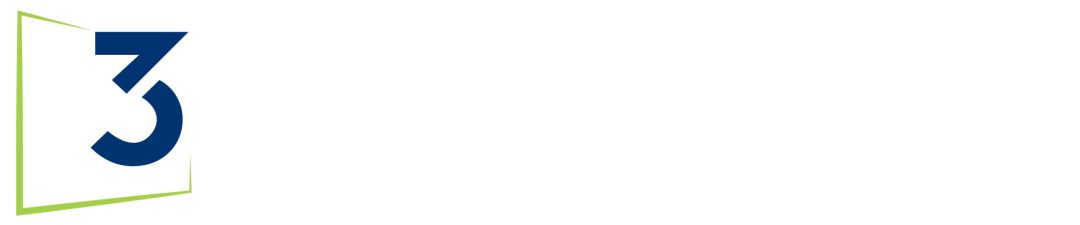
明确规定网络仲裁、间接认可电子送达,限缩“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适用空间
2018年最高法院制定《关于仲裁机构“先予仲裁”裁决或者调解书立案、执行等法律适用问题的批复》,明确“仲裁机构在仲裁过程中未保障当事人申请仲裁员回避、提供证据、答辩等仲裁法规定的基本程序权利的”属于“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程序违反法定程序”,属于不予执行的事由。
实践中,有些法院认为虽然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规定了网络仲裁、电子送达等规则,但由于《仲裁法》第15条第3款规定“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而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既未规定网络仲裁程序,也没有规定哪些文书适用电子送达程序,故仲裁规则中此类内容不构成认定仲裁程序合法的依据。进而,未向当事人依法送达仲裁文书,导致当事人未能参加仲裁,仲裁机构缺席作出裁决的,属于违反法定程序而应当不予执行。
本次《仲裁法》修订,明确认可了网络仲裁程序和仲裁规则规定送达方式。修订后《仲裁法》第11条规定,“仲裁活动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但当事人明确表示不同意的除外。仲裁活动通过信息网络在线进行的,与线下仲裁活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第41条明确,“仲裁文件应当以当事人约定的合理方式送达;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送达”。
据此,未来执行机关不能再单纯以采用网络仲裁或者未依民诉法规定送达作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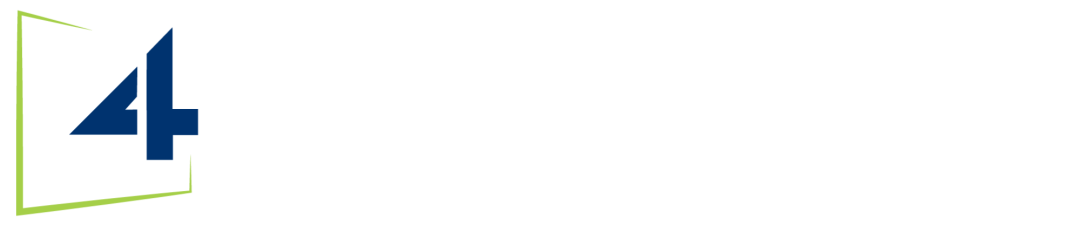
案外人救济路径突破不多
根据修订前的《仲裁法》,只有当事人可以申请撤裁,只有被执行人可以申请不予执行。案外人的权益因仲裁裁决受损的,在法律层面则缺少救济路径。
2018年《仲裁裁决执行规定》创设了案外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为受虚假仲裁裁决不当影响的案外人提供了事后保护。
本次《仲裁法》修订过程中,有专家提出仲裁法应明确仲裁裁决的效力仅约束仲裁的当事人,从源头上避免仲裁裁决对案外人产生不当影响;亦有学者提出增设仲裁第三人制度,希望在仲裁程序为案外人提供“入口”,从而保护其合法权益;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将《仲裁裁决执行规定》中关于案外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内容上升为法律。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则明确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另行起诉两个救济路径。
最终,修订后《仲裁法》仅在第61条对虚假仲裁做了原则性规定,明确仲裁庭发现当事人虚假诉讼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驳回仲裁请求。但就像虚假诉讼在规范层面不乏规制手段,但并不能完全杜绝一样,该条显然也不可能解决全部虚假仲裁问题。相信案外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将是案外人维护自身权利的主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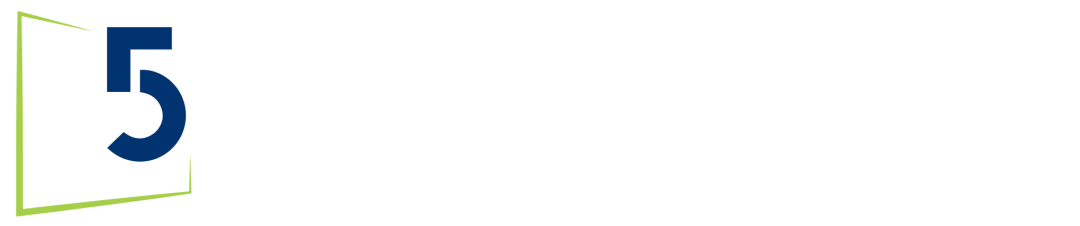
小结
总体来看,本次《仲裁法》对执行部分修订内容有限,像仲裁裁决给付内容不明确应如何处理等问题则完全未予提及。预计未来仲裁裁决执行的相关争议,仍需由执行司法解释、执行工作纪要乃至执行法提供解决方案。
作者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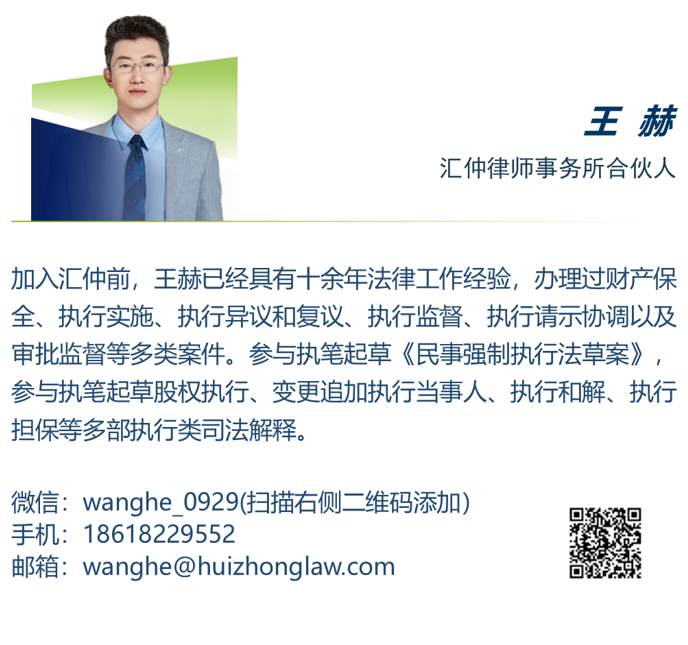
汇仲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注于国内与国际高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精品律所,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设有办公室。汇仲律师十分擅长处理高价值、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与新型跨境案件,他们能够不遗余力地搜寻可以改变判决结果的微小事实,引导案件从绝境到佳境。不论是从案件代理难度、业界口碑还是客户美誉度而言,汇仲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争议解决律师方阵中的一支劲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