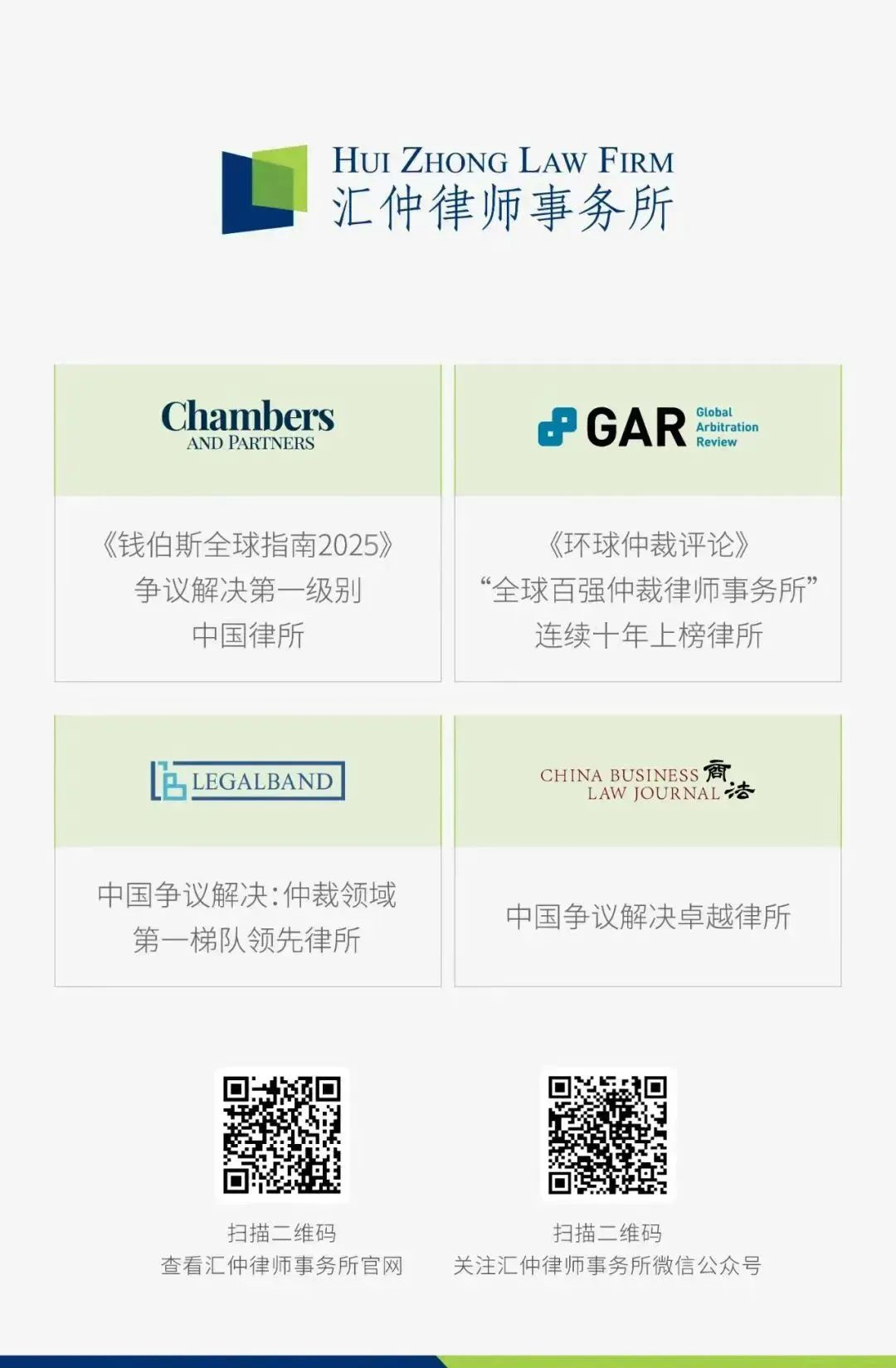文|石睿、畅梗睿
引言:司法理念转变和规则重塑
随着私募基金业务规模不断扩大,银行托管业务也得到较大发展。近年来,金融审判更多参考金融监管规定,更多考虑与金融监管同频共振,此趋势也同样体现在银行托管业务案件中。通过对这些案件的分析,我们列举了若干常见的法律问题,以期相关业务风险防控有所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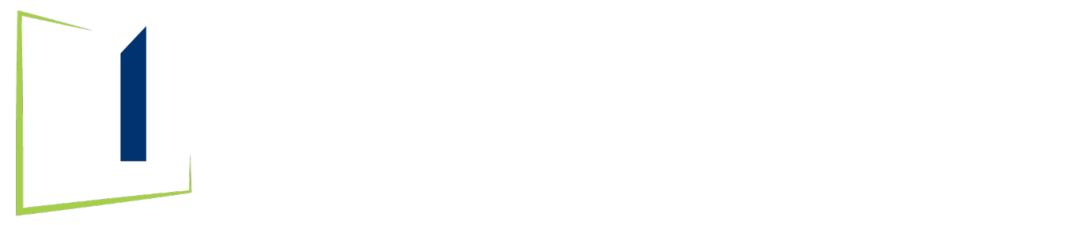 问题一:托管人是否对违规募集或者未登记备案的基金负有审查义务?
问题一:托管人是否对违规募集或者未登记备案的基金负有审查义务?
在基金的募集阶段,主要工作由管理人负责,托管人通常并不参与募集活动。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五条和第十七条之规定,托管人在募集阶段,主要有投资范围等条款的评估、建立托管账户。[1] 实践中,若管理人存在违规募集或未依法登记备案基金等明显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托管人是否应对此履行审查义务并向投资人进行告知?
针对该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多数法院认为,托管人基本不介入基金募集过程,托管协议中也未约定其承担对募集行为的审查义务,因此托管人的责任范围应与管理人相区分,不应过度加重其责任,托管人对此不负有审查义务。[2]
然而,也有判决认定托管人应对基金募集及备案情况履行审查职责。例如,在(2019)京02民终8082号判决中,法院指出,托管人的资产安全保管义务贯穿于基金合同的整个存续期间,作为托管人的光大银行应当了解备案进展,并在资产计划未完成备案时拒绝执行投资指令。该行在未审查合同生效条件是否成就的情况下仍执行指令,对投资人损失存在过错,最终被判承担补充赔偿责任[3]。
笔者认为,上述裁判分歧实质上源于对托管义务开始时间及其来源的不同认定。若将托管义务视为约定义务,即自合同生效或所附条件成就时产生,则托管人仅需依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一般不承担对募集阶段的审查责任。若视托管义务为法定义务,则其起始时间不受合同订立或生效的限制,托管人应自始至终承担审查职责。从金融政策发现变化来看,托管义务被认定为法定义务的趋势逐渐明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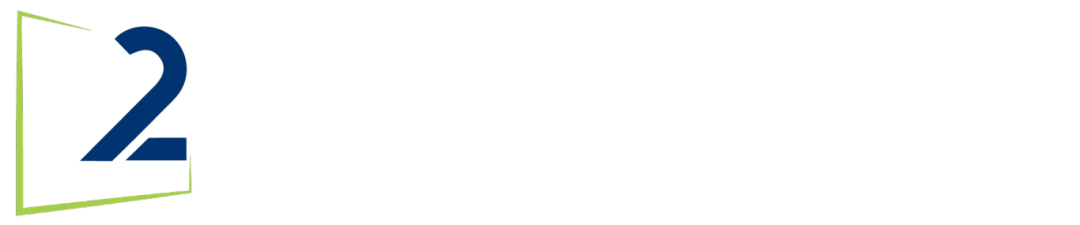
问题二:托管人是否对投资项目的真实性与合规性负有审查义务?
对于这一问题,《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6条规定托管人对指令的审查义务,但未明确规定审查的限度。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合同约定了“表面一致性审查”,多数法院会将合同约定作为确认受托人义务的依据。托管人进行了表面一致性审查,即可认定为尽到了相应的审慎义务。[4]
但也有个别司法判例要求委托人在审查表面一致性外,需要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在指令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托管人应当进行审查。如(2024)沪74民终239号民事判决中,案涉合同中约定银行应对划款指令进行形式审查,二审法院认为,托管人应当持有更加谨慎勤勉的态度,对于如此单一、频繁、高额投向的投资行为,托管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应当知道截图所示的票据信息不完整,未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简单执行划款指令,存在过错。[5]
笔者认为,对于划付指令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由于现行法尚未明确规定,多数法院会以合同约定来确认托管人义务,认可“表面一致性审查”条款的效力。同时,考虑到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在指令明显与合同不符、或者明显不符合商业逻辑的情况下,银行应当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以防止出现重大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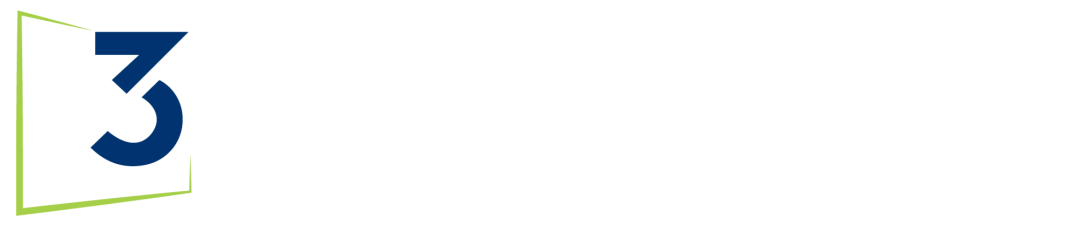
问题三:托管人是否对管理人投资决策失误负有监管义务?
在基金的管理阶段,投资款项已经从托管账户中转出,不再受托管人直接控制,难以控制资金的流向,此时托管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信息披露和相应监管义务。实践中,管理阶段的诉讼多围绕监管义务的边界展开。
依据《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21条之规定,托管人应当依据基金合同及托管协议约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风格”“投资限制”“关联方交易”等进行监督[6]。至于管理人的投资决策行为,现行法未有明确规定。
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会根据合同约定内容来判断托管对管理人监管义务的边界。如果合同没有约定,托管人将款项划转之后,资金已经脱离其掌控,对于后续管理人的投资决策,托管人并不承担监管义务。如(2021)沪74民终1783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资金已经按照约定投入,再要求托管银行监管用资情况,明显超越托管人权责范围。[7]在(2018)粤0304民初31073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托管人对划款指令进行表面一致性审查,已经尽到义务,其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不承担责任。[8]
但如果托管人明知管理人存在不当行为,却未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采取必要动作,则可能会被认定为行为不当。如(2019)湘02民终2404号中,法院认为光大银行作为托管人,其职责在于保证基金的财产安全和监督基金运作,但是其未对汉红基金进行必要的审查和监督,在托管中存在过失,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9]
因此,托管银行对于资金流向明显不符合合同约定、不符合商业逻辑、违法违规的,建议及时审查并告知托管人,避免被认定为重大过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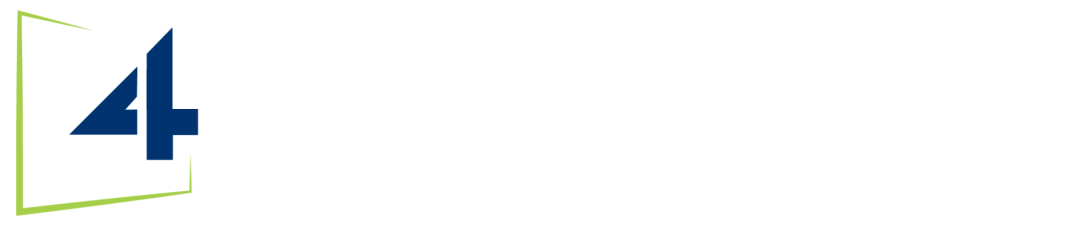
问题四:托管人是否对基金运作信息负有披露义务?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10]规定管理人和托管人均具有披露义务。在基金的管理阶段,投资运作信息主要由管理人掌握,因此管理人负有主要披露义务。依照《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同时托管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托管义务,其披露义务包括对管理人的披露进行复核确认、出具托管人年度报告、对重大事项发布临时报告[11]。
实践中,法院多根据合同约定内容,来判断信息披露义务的范围。如在(2021)沪0115民初75478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托管人已经对划款指令进行核查,根据合同约定,风险控制、风险披露等并非托管人义务。[12]在(2020)鲁1311民初180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托管人未尽到合同约定的基金报告复核、信息披露等义务,未尽到监督投资运作的义务,属于严重失职或积极帮助行为[13]。
但是,如果基金运作过程中发生对投资人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托管人应当及时披露。如果托管人的披露义务需要依托于管理人的材料,托管人也应当及时督促管理人提供。如(2024)沪0115民初20298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基金回款、运营不乐观等属于影响委托人利益的重大事项,虽然该事项的披露应属的管理人的义务,但如若托管人了解相关情况,也应当给予勤勉尽责义务进行披露。[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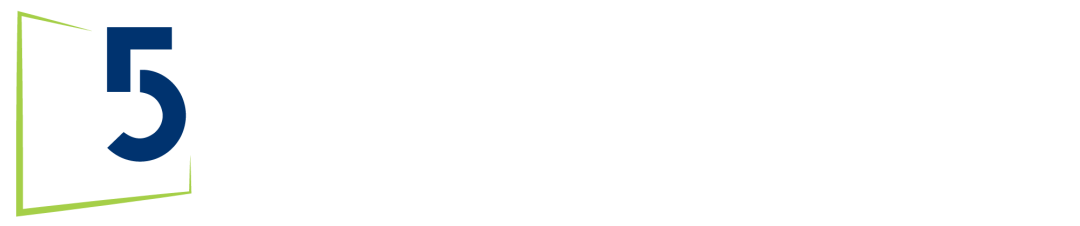
问题五:托管人是否在管理人失联等异常情况时负有审查、监督等义务?
对于这一问题,法院也多以合同约定为主,根据合同判断管理人监管义务的范围。如(2021)沪0115民初112270号民事判决中,管理人因失联被中基协注销,投资人认为托管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法院认为,案涉基金合同约定了平安银行对管理人投资的监管义务,而平安银行在发现管理人失联后,及时向中基协及监管机构报告情况,并在官网对被注销管理人进行披露,已经充分履行了义务。[15]
同时,法院可能会考虑托管人义务履行情况和损害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在(2024)沪0115民初20298号案中,法院认为案涉基金属于集资诈骗和非吸的范围,在管理人失联后,托管人是否审查净值、召集大会,均与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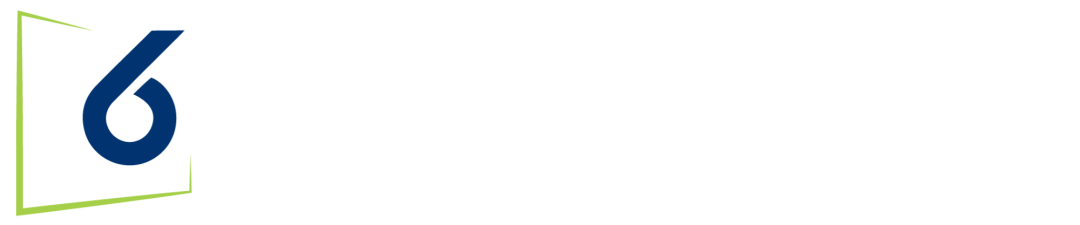
问题六:托管人是否在管理人不履职时负有清算义务?
清算程序关系到资产的有序退出,现行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基金的清算人,基金合同通常约定,由管理人启动清算程序,管理人和托管人共同成立小组。但在管理人不启动清算程序时,托管人是否负有清算义务?
多数法院认为,在管理人不履行清算义务时,托管人在清算阶段仅负有辅助性和补充性责任,并不负有清算的义务。但托管人应及时通报委托人,并向主管部门汇报。如在(2021)沪0115民初97875号案件中,合同约定托管人在清算阶段的相关义务,均以基金管理人履行义务为前提。基金到期后,托管人已催告管理人成立清算小组。同时,也并无证据证明投资人的损失系上海银行的原因造成。[17]
如果合同特别约定托管人在管理人不履职时可独立主持清算的,应依照合同约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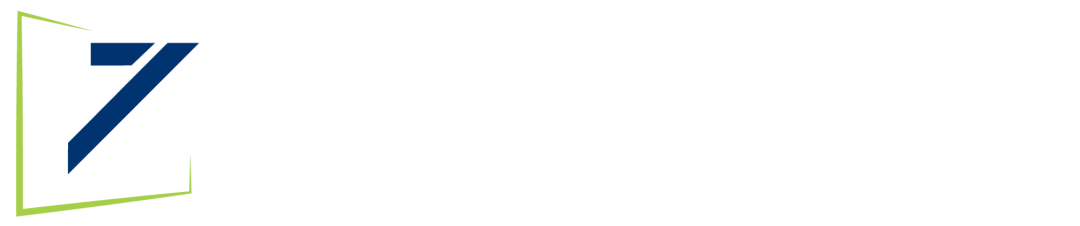
问题七:托管人是否以项目清算为前提承担责任?
通常来说,投资人损失的确定以项目清算为前提。但若存在账户冻结、保全等情况时,项目往往拖延或无法清算,此时投资人能否主张托管人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实践中法院通常以“损失”确定标准作为判断管理人和托管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依据。如果不经过清算,不能确定投资人的损失,法院通常会以损失无法确定为由,不支持投资人的主张。如在(2022)津02民终1472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案涉基金尚未清算,现有证据并不能证明投资人的损失情况,因此驳回起诉。[18]在(2023)沪74民终152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同样认为基金尚未清算,投资损失尚未确定,也难以证明损失和托管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9]
如果项目未做清算,但损失已经确定,仍可判令其承担责任。如(2021)沪74民终375号民事判决中,法院认为清算结果不是认定损失的唯一因素,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投资损失情况的,法院可以依法认定损失。[20]在无法清算的情况下,法院根据投资款、认购费、资金占用利息等确定损失,并明确清算中的清偿应予抵扣,符合损失填平原则。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损失”确定标准。投资者的损失确定通常以清算为前提,但在清算存在困难,投资损失可通过其他因素确定的情况下,托管人的责任承担并不以清算为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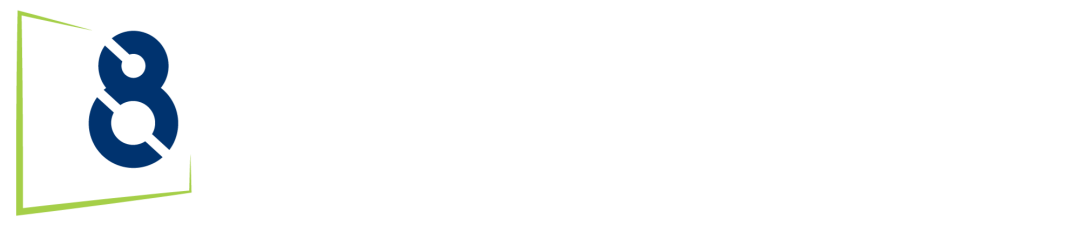
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建议银行在托管时按照“依法履职,持续关注,合理审慎,及时报告”的原则,从以下几方面防控相关风险:
针对签约阶段,法院大多依据合同约定,判断托管人职责边界,因此银行在合同签约阶段,应当注意合同约定内容,包括审查交易主体资质及相关文件,关注其与资金投向的关系;细化托管人义务约定,尤其是明确托管人与管理人的职责划分;细化风险提示内容,尤其是托管人承担责任的条件、内容和范围。
针对托管阶段,在划款前,应从基金备案和资金流向两方面关注:一方面,注意审查基金是否成立、是否备案、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的其他前置条件,注意区分“募集户”和“托管户”;另一方面,注意审查资金投向与合同约定是否一致,关注资金投向的合理性;如果资金投向风险较大,可要求管理人进一步说明或补充必要材料。划款后,在基金管理阶段,托管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进行信息披露和复核核算:如果管理人或投资项目发生风险事件或舆情,及时联系管理人;如管理人不配合,按照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向有关部门或投资人汇报。在基金退出阶段,按照合同约定配合管理人进行清算,如果管理人履职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失联,及时依约进行信息披露并向有关部门汇报。
*本文在石睿律师的指导下,由实习生畅梗睿负责起草撰写。
注释

声明:本文观点仅供参考,不可视为汇仲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如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或需要法律意见,请与本所联系。
汇仲律师事务所是一家专注于国内与国际高端民商事争议解决的精品律所,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新加坡设有办公室。汇仲律师十分擅长处理高价值、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与新型跨境案件,他们能够不遗余力地搜寻可以改变判决结果的微小事实,引导案件从绝境到佳境。不论是从案件代理难度、业界口碑还是客户美誉度而言,汇仲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中国争议解决律师方阵中的一支劲旅。